1. 求徐志摩《猛虎集》中的序文
在诗集子前面说话不是一件容易讨好的事。
说得近于夸张了自己面上说不过去,过 分谨恭又似乎对不起读者。最干脆的办法是什么话也不提,好歹让诗篇它们自身去承当。
但书店不肯同意;他们说如其作者不来几句序言书店做广告就无从着笔。作者对于生意 是完全外行,但他至少也知道书卖得好不仅是书店有利益,他自己的版税也跟着像样:所以书店的意思,他是不能不尊敬的。
事实上我已经费了三个晚上,想写一篇可以帮助 广告的序。可是不相干,一行行写下来只是仍旧给涂掉,稿纸糟蹋了不少张,诗集的序 终究还是写不成。
况且写诗人一提起写诗他就不由得伤心。世界上再没有比写诗更惨的事;不但惨,而且寒伧。
就说一件事,我是天生不长髭须的,但为了一些破烂的句子,就我也不知曾 经捻断了多少根想象的长须。 这姑且不去说它。
我记得我印第二集诗的时候曾经表示过此后不再写诗一类的话。现在如何又来了一集,虽则转眼间四个年头已经过去。
就算这些诗全是这四年内写的 (实在有几首要早到十三年①份)每年平均也只得十首,一个月还派不到一首,况且又 多是短短一橛的。诗固然不能论长短,如同Whistler②说画幅是不能用田亩来丈量的。
但事实是咱们这年头一口气总是透不长——诗永远是小诗,戏永远是独幕,小说永远是 短篇。每回我望到莎士比亚的戏,丹丁③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一类作品,比 方说,我就不由的感到气馁,觉得我们即使有一些声音,那声音是微细得随时可以用一 个小拇指给掐死的。
天呀!哪天我们才可以在创作里看到使人起敬的东西?哪天我们这 些细嗓子才可以豁免混充大花脸的急涨的苦恼? 说到我自己的写诗,那是再没有更意外的事了。我查过我的家谱,从永乐④以来我 们家里没有写过一行可供传诵的诗句。
在二十四岁以前我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对于相对 论或民约论的兴味。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 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⑤!在二十四岁以前,诗,不论新旧,于我是完全没有相 干。
我这样一个人如果真会成功一个诗人——哪还有什么话说? 但生命的把戏是不可思议的!我们都是受支配的善良的生灵,哪件事我们作得了主?整十年前我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也许照着了什么奇异的月色,从此起我的思想就倾向 于分行的抒写。一份深刻的忧郁占定了我;这忧郁,我信,竟于渐渐的潜化了我的气质。
话虽如此,我的尘俗的成分并没有甘心退让过;诗灵的稀小的翅膀,尽他们在那里 腾扑,还是没有力量带了这整份的累坠往天外飞的。且不说诗化生活一类的理想那是谈 何容易实现,就说平常在实际生活的压迫中偶尔挣出八行十二行的诗句都是够艰难的。
尤其是最近几年有时候自己想着了都害怕:日子悠悠的过去内心竟可以一无消息,不透 一点亮,不见丝纹的动。我常常疑心这一次是真的干了完了的。
如同契玦腊⑥的一身美 是问神道通融得来限定日子要交还的,我也时常疑虑到我这些写诗的日子也是什么神道 因为怜悯我的愚蠢暂时借给我享用的非分的奢侈。我希望他们可怜一个人可怜到底! 一眨眼十年已经过去。
诗虽则连续的写,自信还是薄弱到极点。“写是这样写下了”,我常自己想,“但准知道这就能算是诗吗”?就经验说,从一点意思的晃动到一篇诗的 完成,这中间几乎没有一次不经过唐僧取经似的苦难的。
诗不仅是一种分娩,它并且往 往是难产!这份甘苦是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一个诗人,到了修养极高的境界,如同泰 戈尔先生比方说,也许可以一张口就有精圆的珠子吐出来,这事实上我亲眼见过来的不 打谎,但像我这样既无天才又少修养的人如何说得上? 只有一个时期我的诗情真有些像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
那就是我最早写诗 那半年,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 纷的花雨。我那时是绝无依傍,也不知顾虑,心头有什么郁积,就付托腕底胡乱给爬梳 了去,救命似的迫切,哪还顾得了什么美丑!我在短时期内写了很多,但几乎全部都是 见不得人面的。
这是一个教训。 我的第一集诗——《志摩的诗》——是我十一年⑦回国后两年内写的;在这集子里 初期的汹涌性虽已消灭,但大部分还是情感的无关阑的泛滥,什么诗的艺术或技巧都谈 不到。
这问题一直要到民国十五年我和一多⑧、今甫⑨一群朋友在《晨报副镌》刊行 《诗刊》时方才开始讨论到。一多不仅是诗人,他也是最有兴味探讨诗的理论和艺术的 一个人。
我想这五六年来我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响。我 的笔本来是最不受羁勒的一匹野马,看到了一多的谨严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 性;但我素性的落拓始终不容我追随一多他们在诗的理论方面下过任何细密的工夫。
我的第二集诗——《翡冷翠的一夜》——可以说是我的生活上的又一个较大的波折 的留痕。我把诗稿送给一多看,他回信说“这比《志摩的诗》确乎是进步了——一个绝 大的进步”。
他的好话我是最愿意听的,但我在诗的“技巧”方面还是那楞生生的丝毫 没有把握。 最近这几年生活不仅是极平凡,简直是到了枯窘的深处。
跟着诗的产量也。
2. 徐志摩与《猛虎集》
《猛虎集》(1931)是徐志摩出版了的第三部诗集,也是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诗集。
徐志摩 (1897~1931)现代诗人、散文家。名章垿,笔名南湖、云中鹤等。
浙江海宁人。1915年毕业于杭州一中、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
1918年赴美国学习银行学。1921年赴英国留学,入伦敦剑桥大学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
在剑桥两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 1921年开始创作新诗。
1922年返国后在报刊上发表大量诗文。1923年,参与发起成立新月社。
加入文学研究会。1924年与胡适、陈西滢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任北京大学教授。
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时任翻译。1925年赴欧洲、游历苏、德、意、法等国。
1926年在北京主编《晨报》副刊《诗镌》,与闻一多、朱湘等人开展新诗格律化运动,影响到新诗艺术的发展。同年移居上海,任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教授。
1927年参加创办新月书店。次年《新月》月刊创刊后任主编。
并出国游历英、美、日、印诸国。1930年任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委员,被选为英国诗社社员。
同年冬到北京大学与北京女子大学任教。1931年初,与陈梦家、方玮德创办《诗刊》季刊,被推选为笔会中国分会理事。
同年11月19日,由南京乘飞机到北平,因遇雾在济南附近触山,机坠身亡。著有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散文集《落叶》、《巴黎的鳞爪》、《自剖》、《秋》,小说散文集《轮盘》,戏剧《卞昆冈》(与陆小曼合写),日记《爱眉小札》、《志摩日记》,译著《曼殊斐尔小说集》等。
他的作品已编为《徐志摩文集》出版。徐诗字句清新,韵律谐和,比喻新奇,想象丰富,意境优美,神思飘逸,富于变化,并追求艺术形式的整饬、华美,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为新月派的代表诗人。
他的散文也自成一格,取得了不亚于诗歌的成就,其中《自剖》、《想飞》、《我所知道的康桥》、《翡冷翠山居闲话》等都是传世的名篇。《猛虎集》序 在诗集子前面说话不是一件容易讨好的事。
说得近于夸张了自己面上说不过去,过分谨恭又似乎对不起读者。最干脆的办法是什么话也不提,好歹让诗篇它们自身去承当。
但书店不肯同意;他们说如其作者不来几句序言书店做广告就无从着笔。作者对于生意是完全外行,但他至少也知道书卖得好不仅是书店有利益,他自己的版税也跟着像样:所以书店的意思,他是不能不尊敬的。
事实上我已经费了三个晚上,想写一篇可以帮助广告的序。可是不相干,一行行写下来只是仍旧给涂掉,稿纸糟蹋了不少张,诗集的序终究还是写不成。
况且写诗人一提起写诗他就不由得伤心。世界上再没有比写诗更惨的事;不但惨,而且寒伧。
就说一件事,我是天生不长髭须的,但为了一些破烂的句子,就我也不知曾经捻断了多少根想象的长须。 这姑且不去说它。
我记得我印第二集诗的时候曾经表示过此后不再写诗一类的话。现在如何又来了一集,虽则转眼间四个年头已经过去。
就算这些诗全是这四年内写的(实在有几首要早到十三年①份)每年平均也只得十首,一个月还派不到一首,况且又多是短短一橛的。诗固然不能论长短,如同whistler②说画幅是不能用田亩来丈量的。
但事实是咱们这年头一口气总是透不长——诗永远是小诗,戏永远是独幕,小说永远是短篇。每回我望到莎士比亚的戏,丹丁③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一类作品,比方说,我就不由的感到气馁,觉得我们即使有一些声音,那声音是微细得随时可以用一个小拇指给掐死的。
天呀!哪天我们才可以在创作里看到使人起敬的东西?哪天我们这些细嗓子才可以豁免混充大花脸的急涨的苦恼? 说到我自己的写诗,那是再没有更意外的事了。我查过我的家谱,从永乐④以来我们家里没有写过一行可供传诵的诗句。
在二十四岁以前我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⑤!在二十四岁以前,诗,不论新旧,于我是完全没有相干。
我这样一个人如果真会成功一个诗人——哪还有什么话说? ①十三年,指民国十三年,即1924年。 ②whistler,通译惠斯勒(1834—1903),美国画家。
他长期侨居英国。 ③丹丁,通译但丁(1265—1321),意大利诗人。
④永乐、明成祖朱棣的年号(1403—1424)。 ⑤hamilton,通译汉密尔顿(1757—1804),美国建国初期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在华盛顿总统任期内先后主持财政和军备工作。
但生命的把戏是不可思议的!我们都是受支配的善良的生灵,哪件事我们作得了主?整十年前我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也许照着了什么奇异的月色,从此起我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一份深刻的忧郁占定了我;这忧郁,我信,竟于渐渐的潜化了我的气质。
话虽如此,我的尘俗的成分并没有甘心退让过;诗灵的稀小的翅膀,尽他们在那里腾扑,还是没有力量带了这整份的累坠往天外飞的。且不说诗化生活一类的理想那是谈何容易实现,就说平常在实际生活的压迫中偶尔挣出八行十二行的诗句都是够艰难的。
3. 猛虎集的诗集简介
诗集。徐志摩著。1931年8月新月书店出版。收诗34首。另有译诗7首。
作者在序文中说那时的创作状态“简直到了枯窘的深处”,然而,“久蛰的性灵”无意中又“摇活了”。这说明,徐志摩到此时已经基本上放弃了对现实的关注,他的诗已经成为“性灵”的挣扎,成为“一刹那间灵感的触发”与“感情的跳跃”,成为单纯的、虚幻的歌,“唱着星月的光辉与人类的希望”。因此,《猛虎集》中的诗篇大多体现出一种飘忽空灵的美,失却了在《志摩的诗》和《翡冷翠的一夜》中本来就飘忽不定的现实意义,同时,迷惘与无奈的意味更加浓厚,成为诗人追求“纯美”的结晶。
脱离现实的作品内容必然是贫瘠的,诗人也一再声称“我知道,我全知道。”但是,他已经完全沉浸在心灵世界中无力自拔,因此,他只有继续痛苦、消耗、枯窘下去。“在妖魔的脏腑内挣扎,/头顶不见一线的天光,/这魂魄,在恐怖的压迫下,/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生活》); “我要在枯秃的笔尖上袅出/一种残破的音调,/为要抒写我的残破思潮。”(《残破》(一))这类诗句就表达了诗人那种无奈却又自赏的心情。然而,《猛虎集》在艺术上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高度。不论是构思的巧妙独特、语言的通脱炼达、意境的深切超逸,都可以说是诗人创作生涯中的高峰。《我等候你》、《再别康桥》、《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等作品,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有着相当高的艺术成就。《再别康桥》一诗,表现了诗人对母校康桥爱恋、陶醉的情致。“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诗的形式单纯统一,韵律柔美自然,语言流畅洒脱,与飘逸动人的艺术形象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轻柔、优美、流动、超然的艺术境界,令人陶醉、令人神往。但是,尽管诗人有着超乎常人的艺术感受力和创造力,以及娴熟的、非凡的艺术技巧,他却始终没能写出反映时代脉搏的诗歌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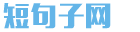 短句子网
短句子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