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传教士与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
一 来华传教士的角色转换与西学东渐 在19世纪中外文化关系中,西方传教士担当了具有双重身份的角色:既是圣经福音的布道者,又是西学东渐的先驱者。
不过其角色身份的重心,有一个转换过程。 通过传播知识以建立信誉、扩大影响,从而利于进一步传教,这种“知识传教”模式,在明清之际利玛窦、艾儒略、南怀仁等来华时就已初步形成。
因此1840年法国天主教重新向中国派出传教士时,“最初计划,是想要在中国重操耶稣会的事业,即科学和传教同时进行”[3]。而此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等,已经在其前辈的基础上开创了“知识传教”的新模式,即把传教和出版书刊、创办学校、开设医院等结合起来。
[4] 他和米怜等创办了第一种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1815),建立了第一个中文印刷机构马六甲印刷 所(1817),开办了第一所中文学校英华书院(1818),翻译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全译本《圣经》(名《神天圣书》,1823),编印了第一部中英文对照辞典《华英字典》(1815— 1823)。《察世俗每月统纪传》曾宣明: 至本报宗旨,首在灌输智识,阐扬宗教,砥砺道德,而国家大事之足以唤醒吾人之迷惘,激发吾人之志气者,亦兼收而并蓄也焉。
本报虽以阐发基督教义为唯一急务,然其他各端,亦未敢视为缓图而掉以轻心。智识科学之于宗教,本相辅而行,足以促进人类之道德,又安可忽视之哉?中国人民之智力,受政治之束缚,而呻吟憔悴无以自拔者,相沿迄今,二千余载,一旦唤起其潜伏之本能,而使之发扬蹈厉,夫岂易事?唯有抉择适当之方法,奋其全力,竭其热忱,始终不懈,庶几能挽回于万一耳。
作始虽简,将毕必巨,若干人创 之于前,则后之学者,责无旁贷矣。是故不揣谫陋,而率尔为之,非冒昧也,不过树之风声,为后人之先驱云尔。
[5] 这段话可以说概括了此后几代传教士的“抉择”。这一“抉择”同时包含着另一层考虑即针对当时中国人“天朝中心主义”的盲目自大心理:“要让中国人了解我们的工艺、科学和原则,从而清除他们那种高傲和排外观念……让中国人确信,他们需要向我们学习很多的东西。”
[6]因此传教士们不仅出版宣传基督教义的普及读物,而且编译了一些“能启迪中国人智力”、“并把西方的技艺和科学传授给他们”[7]的书籍。 早期来华传教士以向中国人介绍世界地理、历史和各国概况为主,很快就产生了效果,突出体现在魏源的《海国图志》。
1852年出版的百卷本《海国图志》征引了编撰者所能见到的古今中外关于世界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著作。若仅就征引书目的种数看,中国的著述是外国人的5倍(所引中国正史及专著近百种,外国人著作及报刊约20种),但是实际引录的文字数量,外国人著述却占了80%。
外国人著述中,明末清初传教士的文字仅占20%,80%的资料来自19世纪前期传教士的著译。摘引最多的是玛吉士的《地理备考》,其次就是马礼逊的《外国史略》、郭实腊(郭士立)《万国地理全图集》、韦理哲《地球图说》、高理文(裨治文)《美里哥(按:即美国)志略》、郭实腊《贸易通志》和《每月统纪传》(即《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以及1850年才开始出版的培瑞(麦嘉缔)编《平安通书》等。
上述著述的作者除玛吉士[8]外,其他均系各国传教士。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推崇《海国图志》说:“中国士大夫之稍有地理知识,实自此始”,“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
而现在我们也可以说,魏源之稍有地理知识,实自传教士始。 同时期另一部重要的世界史地著作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很多资料也来源于传教士雅裨理等。
正是通过他们,中国人打开了了望世界的窗口。 50年代以后,理雅各、伯驾、合信、雒魏林、伟列亚力、艾约瑟、慕维廉等传教士继续推进宗教和知识科学“相辅而行”的方式。
他们创办墨海书馆(上海)、华花圣经书房(宁波)等出版机构,《遐迩贯珍》、《六合丛谈》等杂志,并与中国人合译西书。此期西学传播内容中,自然科学增加,《续几何原本》、《代数学》、《重学》(物理学)、《天文略论》、《全体新论》(解剖学)、《博物新编》、《植物学》等一批影响较大的科学译著先后出版。
同时还开办了一批教会学校,如法国耶稣会创办的上海徐汇公学、美国长 老会创办的登州文会馆等。 不过,19世纪前中叶,大多数传教士仍“以阐发基督教义为第一急务”,出版、教育,还是作为传教的辅助手段。
1843—1860年间香港、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6个城市出版的434种西书中,宗教类占75.8%,若加上相关的道德劝戒类书籍,共占79.5%。其余20.5%非宗教类出版物中,年鉴、杂志、教科书以及语言类等综合性书刊占9.9%;医学、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博物学等自然科学著作34种,占7.8%;各国史地、政经类著译仅12种,只占2.8%。
[9] 可以看出,知识科学所占比例还不大,而且主要是自然科学。 然而到19世纪后期,情况有了较大的改变。
早期传教士来华时,并没有特定侧重的传教对象,但因为在固守儒学传统的官员和文人中受到较大抵制,所以教民大都是下层贫民,其中确也不乏想倚恃教会势力的无业游民。教案的。
2. 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首先,当然是传播了基督教
第二,传播了一些新思想,比如:西医等等
第三,对中国的近代教育也有一定 的影响
第四,大量翻译中国书籍,是中华文化得以传播
传教士除了对中国的教育、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中国的艺术、建筑、科技、外交等方面也都有不少影响。
以下为详细举例
1、外交方面
著名的《尼布楚条约》就是在两位传教士的影响下签订的。在谈判过程中,中方名誉上的全权代表是重臣索额图,俄方代表是戈洛文。但由于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实际上中方直接参与交涉的是葡萄牙人徐日升和法国传教士张诚二人。最后议成的条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徐张二人的影响。
近期研究显示,徐张二人不但参与了与俄方代表的密谈,把中方的大政方针透露给了俄方,而且接受了俄方的贿赂,以至于看似平等的条约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中国的部分利益。沙皇在看到最后条约时甚至喜出望外,俄方代表一干人等也因此加官进爵。
2.艺术方面
这方面最有名的就是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了,其代表作《聚瑞图》、《嵩献英芝图》、《百骏图》(见插图)、《弘历及后妃像》、《平定西域战图》等都堪称清代艺术作品中的精品。郎世宁及其后继者对中国艺术最大的贡献莫过于把西方绘画的透视理念引入了中国传统绘画中,这一影响虽然还不具备从根本上转变中国画理论基础的地步,但也使清代中叶以来诸多中国绘画受到了或多多少的影响,堪称中国绘画艺术上自佛教绘画之后的又一次“新风”了。
3.建筑方面
还是郎世宁,他参与了圆明园西洋楼的设计,为中国古典园林艺术引入了一股新风。著名的大水法就是圆明园西洋楼中的一组景观。
其他参与圆明园西洋楼设计的西方传教士还有法国传教士蒋友仁和王致诚。
4.科技方面
西方传教士在科技方面对中国影响更是多方面的,其中最突出的人物当属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了。
在几何学方面,利玛窦首先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把几何学介绍到了中国。我们今天学习几何时使用的“点、面、线”的概念都是最早由《几何原本》中由来的。很多几何学术语也都是由利玛窦翻译为中文而来的。
在地理学方面,利玛窦印行《山海舆地全图》,首次把向中国介绍了近代地理学。(现代有些研究认为《山海舆地全图》并非利玛窦刊行,存疑)
除了利玛窦,先付后继的西方西方传教士也相继把西方水利、天文、数学、物理学、化学、测绘、机械、航海、船舶制造、农作物栽培等其他方面的科技陆续引入中国,可以说是第一批打开中西方科技交流大门的使者。
当然,这些都是进步意义了
至于他们对中国人民的伤害,也是因为他们的到来加之西方的侵入
3. 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首先,当然是传播了基督教第二,传播了一些新思想,比如:西医等等第三,对中国的近代教育也有一定 的影响第四,大量翻译中国书籍,是中华文化得以传播传教士除了对中国的教育、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对中国的艺术、建筑、科技、外交等方面也都有不少影响。以下为详细举例1、外交方面 著名的《尼布楚条约》就是在两位传教士的影响下签订的。
在谈判过程中,中方名誉上的全权代表是重臣索额图,俄方代表是戈洛文。但由于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实际上中方直接参与交涉的是葡萄牙人徐日升和法国传教士张诚二人。
最后议成的条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徐张二人的影响。 近期研究显示,徐张二人不但参与了与俄方代表的密谈,把中方的大政方针透露给了俄方,而且接受了俄方的贿赂,以至于看似平等的条约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中国的部分利益。
沙皇在看到最后条约时甚至喜出望外,俄方代表一干人等也因此加官进爵。 2.艺术方面 这方面最有名的就是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了,其代表作《聚瑞图》、《嵩献英芝图》、《百骏图》(见插图)、《弘历及后妃像》、《平定西域战图》等都堪称清代艺术作品中的精品。
郎世宁及其后继者对中国艺术最大的贡献莫过于把西方绘画的透视理念引入了中国传统绘画中,这一影响虽然还不具备从根本上转变中国画理论基础的地步,但也使清代中叶以来诸多中国绘画受到了或多多少的影响,堪称中国绘画艺术上自佛教绘画之后的又一次“新风”了。 3.建筑方面 还是郎世宁,他参与了圆明园西洋楼的设计,为中国古典园林艺术引入了一股新风。
著名的大水法就是圆明园西洋楼中的一组景观。 其他参与圆明园西洋楼设计的西方传教士还有法国传教士蒋友仁和王致诚。
4.科技方面 西方传教士在科技方面对中国影响更是多方面的,其中最突出的人物当属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了。 在几何学方面,利玛窦首先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把几何学介绍到了中国。
我们今天学习几何时使用的“点、面、线”的概念都是最早由《几何原本》中由来的。很多几何学术语也都是由利玛窦翻译为中文而来的。
在地理学方面,利玛窦印行《山海舆地全图》,首次把向中国介绍了近代地理学。(现代有些研究认为《山海舆地全图》并非利玛窦刊行,存疑) 除了利玛窦,先付后继的西方西方传教士也相继把西方水利、天文、数学、物理学、化学、测绘、机械、航海、船舶制造、农作物栽培等其他方面的科技陆续引入中国,可以说是第一批打开中西方科技交流大门的使者。
当然,这些都是进步意义了至于他们对中国人民的伤害,也是因为他们的到来加之西方的侵入。
4. 近代外国来华的传教士与早期来华的传教士有何不同
明末清初,天主教传人中国,利玛窦是第一个来华的天主教士。
比较有名的还有汤若 望、南怀仁等。由于采取了较为切近中国国情的传教手段,传教活动相当活跃。
公元1584年,中国天主教信徒只有3人;明亡前夕,在华天主教信徒已达38 000人。传教士主观上 要传播基督教,客观上却成为西学东渐的媒介,带来了西方的一些科学技术。
但传教士中绝大多数是神职人员,专职的文教医务工作者极少,出版书籍数量极少,所选题材也大多 适合传教需要,对中国影响有限。只是到了康熙后期,发生了“礼仪之争”,由于罗马教廷的粗暴干涉,激化了中西矛盾,清朝厉行禁教,中外文化交流从此几乎全部中断。
鸦片战争后,西方教会势力以不平等条约为护身符,在中国拓展,传教士构成了近代 中国社会的一股势力。到公元19世纪末,外国传教士在华人数已多达3000余人,其建教 区40个,教会堂60多个,发展教徒80多万人。
大量事实说明,基督教来华的传教士中虽 然不乏像利玛窦这样的传教者,但从总体上看,是自觉地服务于各国的殖民政策,充当了西方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 传教士宣称“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
外国传教士在帝 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中为其收集情报、出谋划策,参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并享有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种种特权。传教士到中国来以战胜者、特权者的姿态骑在中国人民头上。
他们无恶不作。正因为教会势力已经成为长在中国社会身上的毒瘤,随时随地都会有冲 突爆发,所以公元19世纪下半期教案斗争的本质是侵略势力与反抗势力的矛盾,是中国人民爱国主义意识的初步觉醒,而义和团运动是这种矛盾斗争的高潮。
2000年10月1日梵蒂冈教廷以“对基督忠贞不渝的精神”为由,将120名传教士封为 “圣人”。梵蒂冈此次“封圣”的120人中大多死于鸦片战争至义和团运动期间。
他们中的一些人违反当时的中国法令,非法潜入内地传教,充当侵略中国的帮凶,犯下了不可饶恕 的罪行,受到应有的惩罚。 如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神父马赖由于作恶多端、罪行累累,被广西西林县知事依法处死,爆发了“西林教案”,法国借此勾结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又如,法国主教樊国梁在北京聚集了 3 000名教徒,全副武装对付手无寸铁的义和团,屠杀了许多义和团成员和平民。 樊国梁曾说我手上掌握许多义和团头目的名单,而且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
在他的指引下,大批义和团成员被逮捕杀害。可见他们并不是什么“圣人”,而是不折不扣的罪人。
在西方侵略中国的整个过程中,外国教会和传教士充当了侵略势力的急先锋,参与了各种罪恶活动,任何“慈善”的外衣、“圣洁”的面纱,都掩盖不了其真实面目。 现在梵蒂冈不但不对这段历史中的种种罪行有所忏悔,反而把那些对中国人民犯有罪行的传教士及其追随者封为“圣人”,这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和挑衅,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和嘲讽。
5. 中国近代史这本书中的一段话
『近代中国』始于何时?
尽管西方历史与中国历史的会合在十六世纪就已经开始,但其作用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才显现出来。其时西方的强烈活动引起了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因此,学者对于把十六世纪还是十九世纪看作是近代中国的开端这个问题上颇有分歧。一个很有影响的学派,其中主要包括西方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马克思主义学者和许多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学者,把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看作近代中国的起点。这一学派的中国学者认为,这场战争标志着外国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起点,此后的中国历史便主要是一部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西方历史学家认为,这场战争意味着外国在华活动的加剧,这些活动打破了中国的孤立局面,并在中国开创一个革命性变化的时代。而马克思主义学者则认为,这场战争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之凶恶的缩影,它把『半封建』的中国拖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
第二个学派,主要由一些较为传统的中国史学家组成 (他们的意见有些已开始为西方学者所认同)。他们对以鸦片战争是一个新时代开端此一观点提出挑战。他们认为:以明 (1368—1643年) 清 (1644—1911年)两代交替时期欧洲探险家和传教士来华那段时期作为近代中国的起点会来得恰当,因为,就内部事态而言,该时期适逢满族的兴起和清王朝的建立;就外部局势而言,这一时期西学开始传入中国。他们争辩说,尽管西方的影响在十九世纪发挥了极其巨大的作用,但这只不过是两个半世纪前业已启动的进程的延伸和强化而已,而且鸦片战争之后的百多年的时间,也难以体现一部四千年历史的近代时期。此外,界定近代中国起自于1600年前后的做法,可以使近代中国的开端与近代欧洲的开端趋于一致。
上述这两种观点都有道理,但也都存在一定的缺陷。从影响方面来看,十九世纪西方的冲击在促使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转型上所起的作用,肯定比十六、十七世纪欧洲探险家和传教士到来所起的作用更为巨大。诚然,耶稣会士传人了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制图学和建筑学等西方科学,但他们的影响只局限于中国统治集团内部的一小撮士大夫。他们几乎没有给中国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和经济制度带来任何影响,在这些方面仍然是传教士到来之前的那种模样。从这个角度来说,前一个学派的理由似乎很充足。
但是,如果我们对前期的机构制度不甚了解的话,那么我们将无法全面评判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所发生的各种变化。对西方冲击的研究,必须首先对这种冲击的承受者有所了解。而且,鉴于西方和俄罗斯在影响近代中国命运时,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我们就更不应忽视中国与它们的早期交往所具有的意义,也不应忽略它们所采取的推进方式——西方海权国家从南面向上推进,而陆上大国俄罗斯则从北面向下挺进,它们形成了一种钳形势态,目标直指中国的心脏北京。 确实,从历史回顾的角度来看,十六、十七世纪欧洲人和俄罗斯人的来临,为十九世纪西方的强烈活动铺平了道路。基于这些理由,后一种学派似乎也有可信的论据。
然而,我认为这两个学派可以通过折衷的方法得到调和。即使把鸦片战争界定为近代的起点,我们也仍需熟悉中国传统的国家和社会形态,因为这些形态制约了中国对十九世纪外来挑战所作的反应。西方的入侵可以被视为一种催化剂,促使传统中国转化为近代中国。但是,如果对原先的机制缺乏相当了解的话,我们就很难理解这种转化的效果。

转载请注明出处短句子网 »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精彩短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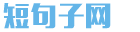 短句子网
短句子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