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五猖会的好词好句及赏析
1原文:在百静中,我似乎头里要伸出许多铁钳,将什么“生于太荒”之流夹住;也听到自己诵读的声音发着抖,仿佛深秋的蟋蟀,在夜中鸣叫似的。
赏析:这是鲁迅先生在即将去东关看五猖会是,却被父亲突然叫住,让他背完一篇古文才准许一家人去的时候心里的感慨。我很同情他,本来是一件很高兴地事,却要背古文,真的是很扫兴,而且又没有人帮助他。从“在百静中”“仿佛深秋的蟋蟀,在夜中鸣叫似的”这些语句中深深体会到了作者的无助无奈以及扫兴。
2-昨夜预定好的三道明瓦窗的大船,已经泊在河埠头,船椅、饭菜、茶炊、点心盒子,都在陆续搬下去了。我笑着跳着,催他们要搬得快。
点评: 突出了少年鲁迅想要观看五猖会的迫切、激动的心情。
3。给我读熟。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我似乎从头上浇了一盆冷水。
点评:突出了观照当今手法翻新、千奇百怪、景象迷离的少年儿童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严酷现实。
4 我却并没有他们那么高兴。开船以后,水路中的风景,盒子里的点心,以及到了东关的五猖会的热闹,对于我似乎都没有什么大意思。
点评:小小孩儿心里那点高兴劲儿,早就一扫而空了。 描写了该教育扼杀了儿童的童趣,又给整个人生留下了不好的回忆。可以说鲁迅的人生是不完整的,本该留藏于脑海的小时候那美好的回忆因为那种教育体制而完全变味。
2. 《五猖会》的好词好句
五猖会
孩子们所盼望的,过年过节之外,大概要数迎神赛会的时候了。但我家的所在很偏僻,待到赛会的行列经过时,一定已在下午,仪仗之类,也减而又减,所剩的极其寥寥。往往伸着颈子等候多时,却只见十几个人抬着一个金脸或蓝脸红脸的神像匆匆地跑过去。于是,完了。
我常存着这样的一个希望:这一次所见的赛会,比前一次繁盛些。可是结果总是一个“差不多”;也总是只留下一个纪念品,就是当神像还未抬过之前,化一文钱买下的,用一点烂泥,一点颜色纸,一枝竹签和两三枝鸡毛所做的,吹起来会发出一种刺耳的声音的哨子,叫作“吹都都”的,吡吡地吹它两三天。
赛会虽然不象现在上海的旗袍,北京的谈国事,为当局所禁止,然而妇孺们是不许看的,读书人即所谓士子,也大抵不肯赶去看。只有游手好闲的闲人,这才跑到庙前或衙门前去看热闹;我关于赛会的知识,多半是从他们的叙述上得来的,并非考据家所贵重的“眼学”。然而记得有一回,也亲见过较盛的赛会。开首是一个孩子骑马先来,称为“塘报”;过了许久,“高照”到了,长竹竿揭起一条很长的旗,一个汗流浃背的胖大汉用两手托着;他高兴的时候,就肯将竿头放在头顶或牙齿上,甚而至于鼻尖。其次是所谓“高跷”、“抬阁”、“马头”了;还有扮犯人的,红衣枷锁,内中也有孩子。我那时觉得这些都是有光荣的事业,与闻其事的即全是大有运气的人,——大概羡慕他们的出风头罢。我想,我为什么不生一场重病,使我的母亲也好到庙里去许下一个“扮犯人”的心愿的呢?……然而我到现在终于没有和赛会发生关系过。
要到东关看五猖会去了。这是我儿时所罕逢的一件盛事,因为那会是全县中最盛的会,东关又是离我家很远的地方,出城还有六十多里水路,在那里有两座特别的庙。一是梅姑庙,就是《聊斋志异》所记,室女守节,死后成神,却篡取别人的丈夫的;现在神座上确塑着一对少年男女,眉开眼笑,殊与“礼教”有妨。其一便是五猖庙了,名目就奇特。据有考据癖的人说:这就是五通神。然而也并无确据。神像是五个男人,也不见有什么猖獗之状;后面列坐着五位太太,却并不“分坐” ,远不及北京戏园里界限之谨严。其实呢,这也是殊与“礼教”有妨的,——但他们既然是五猖,便也无法可想,而且自然也就“又作别论”了。
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
3. 朝花夕拾五猖会好词好句
生命是盛开的花朵,它绽放得美丽,舒展,绚丽多资;生命是精美的小诗,清新流畅,意蕴悠长;生命是优美的乐曲,音律和谐,宛转悠扬;生命是流淌的江河百,奔流不息,滚滚向前。
生活如花,姹紫嫣红;生活如歌,美妙动听;生活如酒,芳香清醇;生活如诗,意境深远,绚丽多彩。
生活是一位睿智的长者,生活是一位博学的老师,它常常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地为我们指点迷津,给我们人生的启迪。
生命的美丽,永远展现在她的进取之中;就像大树的美度丽,是展现在它负势向上高耸入云的蓬勃生机中;像雄鹰的美丽,是展现在它搏风击雨如苍天之魂的翱翔中;像江河的美丽,是展现在它波涛汹涌一泻千里的奔流中。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需要对别人察颜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了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人生如一本书,应该多一些精彩的细节,少一些乏味的字眼;人生如一支歌,应该多一些昂扬的旋律,少一些忧伤的音符;人生如一幅画,应该多一些亮丽的色彩,少一些灰暗的色调。
希望能够帮到你!
4. 《五猖会》里有哪些好词佳句
我找了些,你看看
1.在百静中,我似乎头里要伸出许多铁钳,将什么“生于太荒”之流夹住;也听到自己诵读的声音发着抖,仿佛深秋的蟋蟀,在夜中鸣叫似的。
2.我忽然似乎已经很有把握,便即站了起来,拿书走进父亲的书房,一气背将下去,梦似的就背完了。
3.可是结果总是一个“差不多”;也总是只留下一个纪念品,就是当神像还未抬过之前,化一文钱买下的,用一点烂泥,一点颜色纸,一枝竹签和两三枝鸡毛所做的,吹起来会发出一种刺耳的声音的哨子,叫作“吹都都”的,吡吡地吹它两三天。
4.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
5.人呢,能直立了,自然是一大进步;能说话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能写字作文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然而也就堕落,因为那时也开始了说空话。说空话尚无不可,甚至于连自己也不知道说着违心之论,则对于只能嗥叫的动物,实在免不得“颜厚有忸怩”。
6.我想,这种照片现在是大约未必还有人收藏着了,尺寸太小,刀伤缩小到几乎等于无,如果不加说明,看见的人一定以为是带些疯气的风流人物的裸体照片,倘遇见孙传芳大帅,还怕要被禁止的。
7.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
5. 五猖会的好句,急
篇目《朝花夕拾》 好词:盼望、大概、偏僻、仗义、匆匆忙忙、繁盛、刺耳、夸大、豪奢、十分古怪 好句:1.我常存着这样的一个希望:这一次所见的寒会,比前一次繁盛些。
2.现在看看《陶魇梦忆》,觉得那时的寒会真是豪奢极了。 3.虽然明人的文章,怕难免有些夸大。
4.于是分头四出寻黑矮汉,寻梢长大汉寻头蛇。 5.寻胖大和尚,寻茁壮夫人,寻姣长妇人,寻青面,寻歪头,寻赤须。
感悟:我感觉五猖会的习俗也是十分古怪有趣。
跟五神会比起来是不分上下。五猖会里扮演的人都是一些当地人 民所崇拜或敬佩的水浒英雄。
装扮一番后,就又在当地载歌载舞,欢聚一堂,当时的情景可比我们中国的一些节日有趣多了! ------------------------------ 五猖会 孩子们所盼望的,过年过节之外,大概要数迎神赛会的时候了。但我家的所在很偏僻,待到赛会的行列经过时,一定已在下午,仪仗之类,也减而又减,所剩的极其寥寥。
往往伸着颈子等候多时,却只见十几个人抬着一个金脸或蓝脸红脸的神像匆匆地跑过去。于是,完了。
我常存着这样的一个希望:这一次所见的赛会,比前一次繁盛些。可是结果总是一个“差不多”;也总是只留下一个纪念品,就是当神像还未抬过之前,化一文钱买下的,用一点烂泥,一点颜色纸,一枝竹签和两三枝鸡毛所做的,吹起来会发出一种刺耳的声音的哨子,叫作“吹都都”的,吡吡地吹它两三天。
现在看看《陶庵梦忆》,觉得那时的赛会,真是豪奢极了,虽然明人的文章,怕难免有些夸大。因为祷雨而迎龙王,现在也还有的,但办法却已经很简单,不过是十多人盘旋着一条龙,以及村童们扮些海鬼。
那时却还要扮故事,而且实在奇拔得可观。他记扮《水浒传》中人物云:“……于是分头四出,寻黑矮汉,寻梢长大汉,寻头陀,寻胖大和尚,寻茁壮妇人,寻姣长妇人,寻青面,寻歪头,寻赤须,寻美髯,寻黑大汉,寻赤脸长须。
大索城中;无,则之郭,之村,之山僻,之邻府州县。用重价聘之,得三十六人,梁山泊好汉,个个呵活,臻臻至至,人马称〖女足〗而行……”这样的白描的活古人,谁能不动一看的雅兴呢?可惜这种盛举,早已和明社一同消灭了。
赛会虽然不象现在上海的旗袍,北京的谈国事,为当局所禁止,然而妇孺们是不许看的,读书人即所谓士子,也大抵不肯赶去看。只有游手好闲的闲人,这才跑到庙前或衙门前去看热闹;我关于赛会的知识,多半是从他们的叙述上得来的,并非考据家所贵重的“眼学”。
然而记得有一回,也亲见过较盛的赛会。开首是一个孩子骑马先来,称为“塘报”;过了许久,“高照”到了,长竹竿揭起一条很长的旗,一个汗流浃背的胖大汉用两手托着;他高兴的时候,就肯将竿头放在头顶或牙齿上,甚而至于鼻尖。
其次是所谓“高跷”、“抬阁”、“马头”了;还有扮犯人的,红衣枷锁,内中也有孩子。我那时觉得这些都是有光荣的事业,与闻其事的即全是大有运气的人,——大概羡慕他们的出风头罢。
我想,我为什么不生一场重病,使我的母亲也好到庙里去许下一个“扮犯人”的心愿的呢?……然而我到现在终于没有和赛会发生关系过。 要到东关看五猖会去了。
这是我儿时所罕逢的一件盛事,因为那会是全县中最盛的会,东关又是离我家很远的地方,出城还有六十多里水路,在那里有两座特别的庙。一是梅姑庙,就是《聊斋志异》所记,室女守节,死后成神,却篡取别人的丈夫的;现在神座上确塑着一对少年男女,眉开眼笑,殊与“礼教”有妨。
其一便是五猖庙了,名目就奇特。据有考据癖的人说:这就是五通神。
然而也并无确据。神像是五个男人,也不见有什么猖獗之状;后面列坐着五位太太,却并不“分坐” ,远不及北京戏园里界限之谨严。
其实呢,这也是殊与“礼教”有妨的,——但他们既然是五猖,便也无法可想,而且自然也就“又作别论”了。 因为东关离城远,大清早大家就起来。
昨夜预定好的三道明瓦窗的大船,已经泊在河埠头,船椅、饭菜、茶炊、点心盒子,都在陆续搬下去了。我笑着跳着,催他们要搬得快。
忽然,工人的脸色很谨肃了,我知道有些蹊跷,四面一看,父亲就站在我背后。 “去拿你的书来。”
他慢慢地说。 这所谓“书”,是指我开蒙时候所读的《鉴略》。
因为我再没有第二本了。我们那里上学的岁数是多拣单数的,所以这使我记住我其时是七岁。
我忐忑着,拿了书来了。他使我同坐在堂中央的桌子前,教我一句一句地读下去。
我担着心,一句一句地读下去。 两句一行,大约读了二三十行罢,他说:—— “给我读熟。
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 他说完,便站起来,走进房里去了。
我似乎从头上浇了一盆冷水。但是,有什么法子呢?自然是读着,读着,强记着,——而且要背出来。
粤有盘古,生于太荒, 首出御世,肇开混茫。 就是这样的书,我现在只记得前四句,别的都忘却了;那时所强记的二三十行,自然也一齐忘却在里面了。
记得那时听人说,读《鉴略》比读《千字文》、《百家姓》有用得多,因为可以知道从古到今的大概。知道从古到今的大概,那当然是很好的,然而我一字也不懂。
“粤自盘古”就是“粤自盘古”,读下去,记住它, “粤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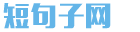 短句子网
短句子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