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欧阳江河的介绍
欧阳江河,男,汉族,1956生于四川省泸州市,原名江河,著名朦胧派诗人。11979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1983年至1984年间,他创作了长诗《悬棺》。其代表作有《玻璃工厂》,《计划经济时代的爱情》,《傍晚穿过广场》,《最后的幻象》,《椅中人的倾听与交谈》,《咖啡馆》,《雪》等。著有诗集《透过词语的玻璃》,《谁去谁留》,《事物的眼泪》、评论集《站在虚构这边》,其写作理念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诗坛有较大的影响,现居北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2. 求欧阳江河的诗歌《蛇》
蛇
欧阳江河
肉体即环绕。
冬眠之后,风景更痛了。
在痛中,蛇是最微弱的。
火焰的舌头,水的腰。
首尾之间,腰在延长。
所有的词语中,一个词在延长,
在耽误,引伸,蠕动。
所有的苹果中的一个苹果。
天堂即悬挂,
腰的诱惑弱于水。
词根的蛇,众词之词,纸的挪动。
掌上无水,水下无脚,
匆匆行走连脚也多余。
春天沿着腹部的闪电到来,
伸展在委屈里,
缠绵于得体的空虚。
禁止的苹果被手环绕,
语言被舌头,爱情被腰。
首尾衔接的时间。
软组织长出了硬骨头,
怕痛的人,终不免一痛。
来自蛇尾的头颅,无一不是老虎。
作者简介
欧阳江河,男,1956生于四川省泸州市,原名江河,著名朦胧派诗人。1979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1983年至1984年间,他创作了长诗《悬棺》。其代表作有《玻璃工厂》,《计划经济时代的爱情》,《傍晚穿过广场》,《最后的幻象》,《椅中人的倾听与交谈》,《咖啡馆》,《雪》等。著有诗集《透过词语的玻璃》,《谁去谁留》,《事物的眼泪》、评论集《站在虚构这边》,其写作理念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诗坛有较大的影响,现居北京。
3. 欧阳江河的诗坛作为
当时由北大五四文学协会刊印的两卷本半官方性质的诗歌刊物《新诗潮诗选》选登了以“欧阳江河”为笔名的三首诗歌:《履历》、《白色之恋》、《背影里的一夜》。而在此之前,作者一直以自己的原名江河发表作品,有趣的是,这个名字恰好就是著名朦胧诗人于友泽的笔名。在1986-1989年期间,欧阳江河的名字开始频频出现于《诗刊》等官方刊物,并且以《现代汉诗》、《日日新》、《诗刊》等杂志为主要载体,发表了一系列诗作与诗歌评论文章,并参与针对“非非主义”等诗歌流派的论战,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欧阳江河在国内建立了自己一流先锋诗人和诗评家的地位。
4. [悬赏] 求高手解析欧阳江河的《谁去谁留》
这首诗歌无不提示着这个世界的分裂性,破碎性和埋葬神性的非神圣性.在这一被诗人出示的世界图景中,每个执著的行为都因其执著而呈现着某种喜剧性.小男孩敏感于这个世界的"机器的心脏",不在倾心于与世界的交流,所以"发明了自己身上的聋";与此相对照的父亲,那个"被..美惊呆了"的人,虽相信世界,并意欲交流,但却被派个''埋头修理"的命运.古典的和现代的,通过两代人的对照被置于一种很微妙的关系之中.古典的坚持而迟钝,现代的敏感而放弃,由此构成一种非对立的张力.某种喜剧中的悲剧意味也开始在诗歌中流溢.最后在诗歌的临终处,"母亲"突然出场了,这使得"谁去谁留"的选择不那么重要了.这个世界除了有必然的"天之将黑,老之将至"外,还有绝对的价值,真理以其绝对正确的选择吗?
5. 欧阳江河的别人评价
如果从一个诗人的才能看,欧阳江河无疑是当代“活着的诗人”中最具综合和整体性能力的一个,他总是能够在历史需要的时候贡献出那种具有重要作用的作品——比如《汉英之间》、比如《傍晚穿过广场》,比如《关于市场经济的虚构笔记》等等。他不但能够用哲学与思辨的方式来处理当代文化与历史的重大命题,而且能够运用具有巨大时代与文化载力的符号,来使这种处理形象化,并同时呈现出思考于其中的复杂而睿智的诗人主体的形象,从而使之上升为一种时代与精神的元命题。这种具有知识分子的自由与自主精神与反思力量的“真正的政治抒情诗”,是欧阳江河的一个重大贡献,在历史的转折时期,他的上述诗歌几乎成为了精神的制高点。出色的智性始终是欧阳江河最闪光的素质,他绵延的语势和滔滔雄辩的语感令人着迷。在“后朦胧诗”时代,他的文本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他的睿智和敏感的诗论文字,对于他的重要性而言也是一个重要的证明和补充。
6. 谁手上有欧阳江河的长诗《悬棺》
彗 星 太短促的光芒可以任意照耀。
有时光芒所带来的黑暗比黑暗更多。 屋里的灯衰弱不均地亮到天明, 而彗星的一生只亮了一瞬, 它的光芒关闭在石头和天空之中。
一颗彗星死了,但与预想无关。 人要走到多高的地方才能坠落? 如空气的目击者俯身向下, 寻找自身曾经消逝的古老痕迹。
我不知道正在消逝的是老人还是孩子 死亡太高深了,让我不敢去死。 一个我们称之为天才的人能活多久? 彗星被与它相似的名称夺走。
时间比突破四周的下颌高出一些, 它迫使人们向上,向高处的某种显露, 向崖顶阴影的漂移之手。 彗星突然亮了,正当我走到屋外。
我没想到眼睛最后会闪现出来, 光芒来得太快,几乎使我瞎掉 遗 忘 越是久远的事物越是清晰可见 苍天在上!苍天里迅速如闪电者 沉入大地的漆黑掩埋,眼里的金子 射向雷霆,从此没有光芒 能够覆盖我的内心而不覆盖我疾速 走过的原野。 春天的原野。
我徒步而行的原野。 迫使一个人用一百只手臂高高举起 马匹和风暴倒下、传开,回声如花叶瓣 的原野。
大地的一个角落 或眼里的几滴泪水。 我从来没有祈求过象现在这么多的泪水。
请允许我比哭泣更低地压低嗓子, 比嗓子更弯曲地弯向大地。 请允许我屈膝而歌,折腰而歌,剜目而歌。
直到瞎了才痛哭的人啊, 将在谁的注目礼中失声痛哭?为谁 而哭?那么伤心地,忍不住地 从生到死地哭!请求别人一起哭! 而那些彻底不眠的夜的攫取者,在白天 是瞎子。他们从太阳吸走了鹰的冷血, 两眼直视太阳象茫无所视。
光亮即遗忘。 我所神往和聆听的、摄我魂魄的年代, 我为之碎身为之悬胆为之歌哭的年代, 是如此久远,倾斜, 象闪电在黑暗的记忆深处那么倾斜, 透过另一个更为倾斜更为久远的年代 的回声,既没有记住,也没有被真正听到。
傍晚穿过广场 我不知道一个过去年代的广场 从何而始,从何而终 有的人用一小时穿过广场 有的人用一生—— 早晨是孩子,傍晚已是垂暮之人 我不知道还要在夕光中走出多远 才能停住脚步? 还要在夕光中眺望多久才能 闭上眼睛? 当高速行驶的汽车打开刺目的车灯 那些曾在一个明媚早晨穿过广场的人 我从汽车的后视镜看见过他们一闪即逝 的面孔 傍晚他们乘车离去 一个无人离去的地方不是广场 一个无人倒下的地方也不是 离去的重新归来 倒下的却永远倒下了 一种叫做石头的东西 迅速地堆积、屹立 不象骨头的生长需要一百年的时间 也不象骨头那么软弱 每个广场都有一个用石头垒起来的 脑袋,使两手空空的人们感到生存的 份量。以巨大的石头脑袋去思考和仰望 对任何人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石头的重量 减轻了人们肩上的责任、爱情和牺牲 或许人们会在一个明媚的早晨穿过广场 张开手臂在四面来风中柔情地拥抱 但当黑夜降临 双手就变得沉重 惟一的发光体是脑袋里的石头 惟一刺向石头的利剑悄然坠地 黑暗和寒冷在上升 广场周围的高层建筑穿上了瓷和玻璃的时装 一切变得矮小了。
石头的世界 在玻璃反射出来的世界中轻轻浮起 象是涂在孩子们作业本上的 一个随时会被撕下来揉成一团的阴沉念头 汽车疾驶而过,把流水的速度 倾泻到有着钢铁筋骨的庞大混凝土制度中 赋予寂静以喇叭的形状 一个过去年代的广场从汽车的后视镜消失了 永远消失了—— 一个青春期的、初恋的、布满粉刺的广场 一个从未在帐单和死亡通知书上出现的广场 一个露出胸膛、挽起衣袖、扎紧腰带 一个双手使劲搓洗的带补丁的广场 一个通过年轻的血液流到身体之外 用舌头去舔、用前额去下磕、用旗帜去覆盖 的广场 空想的、消失的、不复存在的广场 像下了一夜的大雪在早晨停住 一种纯洁而神秘的融化 在良心和眼睛里交替闪耀 一部分成为叫做泪水的东西 另一部分在叫做石头的东西里变得坚硬起来 石头的世界崩溃了 一个软组织的世界爬到高处 整个过程就象泉水从吸管离开矿物 进入密封的、蒸馏过的、有着精美包装的空间 我乘坐高速电梯在雨天的伞柄里上升 回到地面时,我看到雨伞一样张开的 一座圆形餐厅在城市上空旋转 像一顶从魔法变出来的帽子 它的尺寸并不适合 用石头垒起来的巨人的脑袋 那些曾托起广场的手臂放了下来 如今巨人仅靠一柄短剑来支撑 它会不会刺破什么呢?比如,一场曾经有过的 从纸上掀起、在墙上张帖的脆弱革命? 从来没有一种力量 能把两个不同的世界长久地粘在一起 一个反复张帖的脑袋最终将被撕去 反复粉刷的墙壁 被露出大腿的混血女郎占据了一半 另一半是头发再生、假肢安装之类的诱人广告 一辆婴儿车静静地停在傍晚的广场上 静静地,和这个快要发疯的世界没有关系 我猜婴儿和落日之间的距离有一百年之遥 这是近乎无限的尺度,足以测量 穿过广场所要经历的一个幽闭时代有多么漫长 对幽闭的普遍恐惧,使人们从各自的栖居 云集广场,把一生中的孤独时刻变成热烈的节日 但在栖居深处,在爱与死的默默的注目礼中 一个空无人迹的影子广场被珍藏着 像紧闭的忏悔室只属於内心的秘密 是否穿越广场之前必须穿越内心的黑暗 现在黑暗中最黑的两个世界合为一体 坚硬的石头脑袋被劈开 利剑在黑暗中闪闪发光 如果我能用被劈成两半的神秘黑夜 去解释一个双脚踏在大地上的明媚早晨—— 如果我能沿着洒满晨。
7. "在集体的耳朵中我是个聋子"是欧阳江河哪首诗里的
手枪手枪可以拆开拆作两件不相关的东西一件是手,一件是枪枪变长可以成为一个党手涂黑可以成为另外一个党而东西本身可以再拆直到成为相反的向度世界在无穷的拆字法中分离人用一只眼睛寻找爱情另一只眼睛压进枪膛子弹眉来眼去鼻子对准敌人的客厅政治向左倾斜一个人朝东方开枪另一个人在西方倒下黑手党戴上白手套长枪党改用短枪永远的维纳斯站在石头里她的手拒绝了人类从她的胸脯里拉出两只抽屉里面有两粒子弹,一支枪要扣响时成为玩具谋杀,一次哑火最后的幻象(组诗)草莓如果草莓在燃烧,她将是白雪的妹妹。
她触到了嘴唇但另有所爱。没人告诉我草莓被给予前是否荡然无存。
我漫长一生中的散步是从草莓开始的。一群孩子在鲜红迎风的意念里狂奔,当他们累了,无意中回头——这是多么美丽而茫然的一个瞬间!那时我年轻,满嘴都是草莓。
我久已忘怀的青青草地,我将落未落的小小泪水,一个双亲缠身的男孩曾在天空下痛哭。我返身走进乌云,免得让他看见。
两个人的孤独只是孤独的一半。初恋能从一颗草莓递过来吗?童年的一次头晕持续到现在。
情人在月亮盈怀时变成了紫色。这并非一个抒情的时代,草莓只是从牙齿到肉体的一种速度,哦,永不复归的旧梦,谁将听到我无限怜悯的哀歌?花瓶,月亮花瓶从手上拿掉时,并没有妨碍夏日。
它以为能从我的缺少进入更多的身体,但除了月亮,哪儿我也没去过。在月光下相爱就是不幸。
我们曾有过如此相爱的昨天吗?月亮是对亡灵的优雅重获。它闪耀时,好像有许多花儿踮起了足尖。
我看见了这些花朵,这些近乎亡灵的束腰者,但叫不出它们的名字。花瓶表达了直觉,它让错视中的月亮开在水底。
那儿,花朵像一场大火横扫过来。体内的花瓶倾倒,白骨化为音乐。
一曲未终,黑夜已经来临。这只是许多个盈缺之夜的一夜,灵魂的不安在肩头飘动。
当我老了,沉溺于对伤心咖啡馆的怀想泪水和有玻璃的风景混在一起,在听不见的声音里碎了又碎。我们曾经居住的月亮无一幸存,我们双手触摸的花瓶全都掉落。
告诉我,还有什么是完好如初的?落 日落日自咽喉涌出,如一枚糖果含在口中。这甜蜜、销魂、唾液周围的迹象,万物的同心之圆、沉没之圆、吻之圆一滴墨水就足以将它涂掉。
有如漆黑之手遮我双目。哦疲倦的火、未遂的火、隐身的火,这一切几乎是假的。
我看见毁容之美的最后闪耀。落日重重指涉我早年的印象。
它所反映的恐惧起伏在动词中,像抬级而上的大风刮过屋顶,以微弱的姿态披散于众树。我从词根直接走进落日,他曾站在我的身体里,为一束偶尔的光晕眩了一生。
落日是两腿间虚设的容颜,是对沉沦之躯的无边挽留。但除了末日,没有什么能够留住。
除了那些热血,没有什么正在变黑除了那些白骨,没有谁曾经是美人一个吻使我浑身冰凉。世界在下坠,落日高不可问。
黑 鸦幸福是阴郁的,为幻象所困扰。风,周围肉体的杰作。
这么多面孔没落,而秋天如此深情,像一闪而过,额头上的夕阳,先是一片疼痛,然后是冷却、消亡,是比冷却和消亡更黑的终极之爱。然而我们一生中从未有过真正的黑夜在白昼,太阳倾泻乌鸦,幸福是阴郁的,当月亮落到刀锋上,当我们的四肢像泪水洒在昨天反复冻结。
火和空气在屋子里燃烧,客厅从肩膀上滑落下来,往来的客人坐进乌鸦的怀抱。每一只乌鸦带给我们两种温柔。
这至爱的言词:如果爱还来得及说出。我们从未看见比一只乌鸦更多的美丽。
一个赤露的女人从午夜焚烧到天明。蝴 蝶蝴蝶,与我们无关的自怜之火。
庞大的空虚来自如此娇小的身段,无助的哀告,一点力气都没有。你梦想从蝴蝶脱身出来,但蝴蝶本身也是梦,比你的梦更深。
幽独是从一枚胸针的丢失开始的。它曾别在胸前,以便怀华灯初上时能听到温暖的话语,重读一些旧信。
你不记得写信人的模样了。他们当中是否有人以写作的速度在死去,以外的速度在进入?你读信的夜里胸针已经丢失。
一只蝴蝶先是飞离然后返回预兆,带着身体里那些难以解释的物质。想从蝴蝶摆脱物质是徒劳的。
物质即绝对,没有遗忘的表面蝴蝶是一天那么长的爱情,如果加上黑夜,它将减少到一吻。你无从获知两者之中谁更短促:一生,还是一昼夜的蝴蝶?蝴蝶太美了,反而显得残忍。
玫 瑰第一次凋谢后,不会再有玫瑰。最美丽的往往也是最后的。
尖锐的火焰刺破前额,我无法避升这来自冥界的热病玫瑰与从前的风暴连成一片。我知道她向往鲜艳的肉体,但比人们所想象的更加阴郁。
往日的玫瑰泣不成声她溢出耳朵前已经枯萎了。正在盛开的,还能盛开多久?玫瑰之恋痛饮过那么多情人,如今他们衰老得像高处的杯子,失手时感到从未有过的平静。
所有的玫瑰中被拿掉了一朵.为了她,我将错过晚年的幽邃之火如果我在写作,她是最痛的语言。我写了那么多书,但什么也不能挽回仅一个词就可以结束我的一生,正像最初的玫瑰,使我一病多年。
雏 菊雏菊的昨夜在阳光中颤抖。一扇突然关闭的窗户闯进身体,我听见婴孩开成花朵的声音。
裙子如流水,没有遮住什么,正像怀里的雏菊一无所求,四周莫名地闪着几颗牙齿。一个四岁的女孩想吃黄金。
雏菊的片面从事端闪回肉体。雨水与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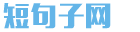 短句子网
短句子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