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求含有“大海”的诗句要有写出自哪里,作者是谁等等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海子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似乎表明诗人要在尘世营造幸福的生活,但诗人又用实际行动拒斥了对生活的介入——这首诗,如果和诗人的具有诗歌史文本意义(或是作为诗歌文本的一种完成)的行为相比较,两个文本之间构成反讽式的分裂。
在这首诗里,纯朴直白的诗句、清新明快的意象未能遮蔽诗人对于“幸福”的抒写中的内在分离和矛盾,对“幸福”的表述在诗歌情绪的延伸中产生了歧变。而诗中的自我申诉也构成反讽式的消解,呈现出诗人的生存及思考中无法逾越的困惑。
“从明天起”表示时间上的断裂,和过去、现在形成间隔,似乎意味着姿态和目光的转移;“从明天起”,语气的断然,像一个单纯的少年在下决心:“从明天起,我要如何如何……”然而诗人已选择了的理性自觉的心灵探索无法轻松地中断。 “做一个幸福的人”,作为一个具有自主自为能力的人,诗人自然有选择生活的自由,他可以选择去感受“幸福”。
这里的“幸福”被限定在日常生活的意义范围内,主要指向满足日常欲望(物质的以及情感的)、享受世俗快乐,例如“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与亲人通信,等等。 可以在“关心粮食和蔬菜”的过程中,感受日常生活本身包含的享受物质快乐、使人休闲放松的内容,欲望的满足具有接近幸福感的可能。
从诗句表层含义看,似乎诗人正走出自我的心灵重轭,试图理解、接受、融入“每一个人”所能理解的“幸福”之中;但同时又矛盾重重。 在诗人心目中,这种“幸福”更多是一种被体验的过程,它距离诗人苦苦追寻的理想境界仍很遥远——“幸福”在这里仍然是一个等同于世俗快乐的、在“尘世”中被追寻的东西(过程)。
“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和物质的短暂情人”(《祖国,或以梦为马》)的诗人不会停留、满足于此。 这一点在第三章中得到明示。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告诉”意味着沟通,和人们交流、讨论关于幸福的感受和体验,没有了“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舒婷《致橡树》)的清高和孤傲;“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精炼地表述了一种体验:我们所能感受到的“幸福”,往往是在一瞬间,如同闪电一般的短暂;而就在“幸福”的那个瞬间,那种感受是如同闪电般的直击心灵,带来巨大的冲击。 这样的激情甚至引发了诗人要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个“温暖的名字”的浪漫想象与冲动,显示了一种“走近”、“亲近”的姿态。
“在海子看来,由于现代文明的畸形,人们无论是在他们所处的时代还是在他们关乎历史的记忆的情境中,都日益丧失了对生命作为一种奇迹的感受能力。 所以,他认为自己有责任通过诗歌来帮助我们恢复对生命的感受力。
洋溢在海子的抒情诗中的种种奇妙而热烈的情感,都与这种审美判断有关。”(臧棣《向神话致意》)。
因而,这种亲近,更多是在与自我生命的内在意识对话,通过这种方式,诗人关心的仍是抽象的命题(这些抽象的命题和思考同样普遍存在于他的诗歌创作和诗歌观念的表述中),具有形而上的指向和自赋的使命感和神圣感,在表面的亲近中透着本真的孤绝。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诗人想象自己有这样一个既可以喂马劈柴关心粮食蔬菜的房子(在现实生活——尘世中的位置),又有一个超离生活之外,眺望大海(超越尘世的理想彼岸)的姿态和空间。
也许,就像他喜爱的梭罗,在瓦尔登湖畔拥有的那座木屋。 这句话在诗的首章末尾出现,表达了既能融入尘世的日常幸福,又保持作形而上之观照和思考的愿望;但在第三章末尾,同样的句子,加了“我只愿”这一表示祈使的词语,却表达了另外一种选择,面朝大海,同时就是背对尘世,他将“在尘世获得幸福”的祝福赠予“陌生人”(或者说是“每一个人”),自己还是坚守自我的空间和姿态。
“春天”,“春暖花开”都是诗人对“幸福”生活的想象之境;“春天”带来“光明的景色”,这是渴望“复活”的诗人(《春天,十个海子全部复活》)想走进的。 在关于“幸福”的感受和想象里,“马”同样是不可或缺的:“我无限的热爱着新的一日/今天的太阳 今天的马 今天的花楸树/使我健康 富足 拥有一生/从黎明到黄昏/阳光充足/胜过一切过去的诗”(《幸福的一日——致秋天的花楸树》)。
但是,“马”在海子诗中又有特别的象征意义,他喜爱以“马”作为自己到达理想之境的载体,如“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和物质的短暂情人/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路上/万人都要将火熄灭 我一人独将此火高高举起/此火为大 开花落英于神圣的祖国/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借此火得度一生的茫茫黑夜”(《祖国,。
2. 朱大可的语言为什么被称为“朱语”
黎明前的吸血鬼:《保卫朱大可》 1.朱大可本身是个文化迷津。
解读朱大可首先要避开对朱语的纠缠。相信我,朱语是种陷井,一个语言的石头阵,目的是阻挡无缘者的骚扰。
2.解读朱大可,即是解读自己。这是他始终受到关注的原因。
朱的文本是时间之水,倒映出的总是读者自身。解读者的悟性和穿透力是避免走火入魔的先决条件。
3.朱大可是当今中国汉语语境中唯一一个以自身悟性串连灵性和魔性的得道高人。他洞察到的真相有三个部分重叠的层面:自身的真相和世界的真相,以及语言的真相。
所谓“朱语”就是整合了东西方智慧的言说策略。由此看,朱语本身是无懈可击的。
说白了,懂得的人一听就懂,不懂得人不懂就是不懂。 4.大家都在谈论朱大可的困境。
谢谢关心。其实这才是朱大可落寞之处。
朱及其文本构成了一个雌雄同体,自给自足的磁力场。如果,朱大可不以入世的姿态切入中国版图,所谓困境只是我们自己的困境罢了。
是我们把自救的压力和危机转嫁到了朱大可身上。如同希望子夜里飞出太阳。
荒诞不经的不是世界的黑夜,而是愚昧的我们自己。 5.说到神学或者信仰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没有神学问题的,有的倒是信仰如同王后的贞操不容怀疑。
所以神从没有从他身边走开过,因为他从没有接近过神。不是不愿而是不能,就像一场绝望的爱情。
我看见他端坐在神的对面,以一种暗恋的表情凝望着远方,出神入化,宛如守身如玉的处子。 赵毅衡:《年年岁岁树不同》 人们惊奇地发现他令人叹服却无从模仿的“朱语”,越发飞扬高蹈,他的不休地惊人的观点,也越发犀利。
张斌璐:《朱大可的精神记忆》 戏仿是“朱语”的紧张修辞本领,朱大可在一系列戏仿实行中,显现出阐释的开放性,他所拒绝的仍旧是权利对阐释无所不圆第倒抑,并希求寄托誊写来完成对自由代价的追索。 孤云:《朱大可:寻求独立声音的表述》 朱大可是时下流行的“酷评”的始作俑者,他的写作风格被人称作“朱语”。
文学批评家胡河清当年称朱大可为“文化恐龙”,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对其思想的评价;而在对文字的创造力上,朱大可更可谓一位“话语高手”。 朱大可的文字瑰丽变幻、富有穿透力,平淡无奇的词语经他排列组合,便魔幻般地具有非凡的力量。
这种语言技巧是长期磨练的结果,朱大可在这上面浸淫了 35年以上的时光。从小学三年级起,他就开始收集语词和佳句,进行语词的打磨。
这种习惯一直到大学还没有抛弃。 颇有意思的是,朱大可小时候还有过轻微的口吃。
或者正是因为如此,朱大可当年选择了以书写作为生命表达的工具。 虽说时下许多写作者模仿朱大可的文字风格,却未必懂得“隐喻式写作”的真谛。
朱大可认为:“批评的力量首先来自准确的判断和估量,其次才是它的隐喻式的组接。话语的力量终究不单单是语词的事务,如果没有语义的支撑,话语的力度是无法获得的。”
夜谭《上海文学批评家导游地图》 才气十足的朱大可被视为学院外人士的代表,他的隐喻式文体因此被一些有志于“院外模式”的文学中青年视为楷模,模仿个不休不歇。翻遍朱大可的文章,满篇皆是隐喻。
因为文体的独特,成为自绝于“学院派”的典型。朱大可的“院外批评”文章,即所谓“朱语”,曾是阳萎的批评界的强力春药,至今仍然暗流涌动。
但也有人把他是视为神学自由主义的范本。 王石《近乎病态的炫技》 评价朱大可,也有许多美誉:敏锐的洞察力和非凡的话语创造力;一种感性和理性交织的隐喻式书写;以标新和立异的风格成为文坛的异数;诡异般的瑰丽文字迷宫;奇怪的话语实验极大地扩张了语言的力度;他的每一次发言都像一道闪电……等等等。
虽然,也有很多人认为,朱大可的写作过于夸饰,过于迷恋惊人之语和炫技。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一个批评环境缺少胆识和诚实态度的年代,朱大可的批评,有着难能可贵的尖锐和锋芒,他的语言所迸发出的才子气,还真不乏“诡异般瑰丽”的诱惑力。
作者不详 理解朱大可,必须从探察他的语言开始。“朱语”打开了通往存在的路,却不告诉人出路在哪,习惯因循的人往往在此迷路。
朱大可是不容易被复制的,被复制的朱大可就象被抽去生命内核的语言,变成一场无关灵魂的语言秀。进入朱大可,就象进入一个慢性绞肉机,必须接受它的绞杀,而且时时寻找对语言城堡的突围。
我至今仍象卡夫卡笔下的土地测量员一样,只能在朱大可语言城堡的外围徘徊。 玻璃村:《“文化恐龙”与野性的思维》 语言是思想投射在文本外部的斑斓面具,如同彩虹只是雨点对光的折射。
一些人注定无法穿越朱语的迷津,他们找不到可以借渡的舟楫。他们研究、模仿、书写着一种貌似朱语的文字符码,频频闪现于朱语常用词汇的现场,却若一个蹩脚的珠宝匠人,因着自我原创思想的严重缺席,茫然无措的面对着一颗颗词汇的珍珠,却无法将词之珠串成语之链。
所以原本便单薄贫血的文本,充斥满词的碎屑。而仅仅纠缠于词,仅仅对朱式词汇进行表面的租借,就以为自己洞穿了朱语的奥秘,这看法与做法显然是幼稚可笑的。
羽戈:《十年来看过的最好看的中国作家的作品》 我的批评路数,大致没有脱出朱大可老师。
3. 语文`.
死火 我梦见自己在冰山间奔驰。
这是高大的冰山,上接冰天,天上冻云弥漫,片片如鱼鳞模样。山麓有冰树林, 枝叶都如松杉。
一切冰冷,一切青白。 但我忽然坠在冰谷中。
上下四旁无不冰冷,青白。而一切青白冰上,却有红影无数,纠结如珊瑚网。
我俯看脚下,有火焰在。 这是死火。
有炎炎的形,但毫不摇动,全体冰结,象珊瑚枝;尖端还有凝固的 黑烟,疑这才从火宅中出,所以枯焦。这样,映在冰的四壁,而且互相反映,化成 无量数影,使这冰谷,成红珊瑚色。
哈哈! 当我幼小的时候,本就爱看快舰激起的浪花,洪炉喷出的烈焰。 不但爱看,还 想看清。
可惜他们都息息变幻,永无定形。虽然凝视又凝视,总不留下怎样一定的 迹象。
死的火焰,现在先得到了你了! 我拾起死火,正要细看,那冷气已使我的指头焦灼;但是,我还熬着,将他塞 入衣袋中间。冰谷四面,登时完全青白。
我一面思索着走出冰谷的法子。 我的身上喷出一缕黑烟,上升如铁线蛇。
冰谷四面,又登时满有红焰流动,如 大火聚,将我包围。我低头一看,死火已经燃烧,烧穿了我的衣裳,流在冰地上了。
“唉,朋友!你用了你的温热,将我惊醒了。”他说。
我连忙和他招呼,问他名姓。 “我原先被人遗弃在冰谷中,”他答非所问地说,“遗弃我的早已灭亡,消尽 了。
我也被冰冻冻得要死。倘使你不给我温热,使我重行烧起,我不久就须灭亡。”
“你的醒来,使我欢喜。我正在想着走出冰谷的方法;我愿意携带你去,使你 永不冰结,永得燃烧。
” “唉唉!那么,我将烧完!” “你的烧完,使我惋惜。我便将你留下,仍在这里罢。”
“唉唉!那么,我将冻灭了!” “那么,怎么办呢?” “但你自己,又怎么办呢?”他反而问。 “我说过了:我要出这冰谷……” “那我就不如烧完!” 他忽而跃起,如红慧星,并我都出冰谷口外。
有大石车突然驰来,我终于碾死 在车轮底下,但我还来得及看见那车坠入冰谷中。 “哈哈!你们是再也遇不着死火了!”我得意地笑着说,仿佛就愿意这样似的。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
4. 看文学有什么用
文学在我们生活中的意义在哪里呢?看看陀斯妥耶夫斯基是怎么说的:“没有文学,我可能早就疯了,或者已经死去。”
他是这样谈文学的,文学就是他的勇气、他的希望。同样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索尔仁尼琴、艾赫马托娃,等等,他们都是在压力下依靠写作活下来的人。
1947年,思想家以撒·伯林到莫斯科访问,会见艾赫马托娃,他们长谈一晚。次日,艾赫马托娃在日记中写道:“终于找到一个人可以谈这些事,尽管没有价值,但我 现代心灵需要文学理疗 现代人彼此交流的机会也许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
现代人看似坚强、冷漠,其实更容易孤独,更容易寂寞。也正因此,文学这种间接的精神交流形式对现代人来说变得越发重要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世纪以来,西方许多世界级的哲学大师、思想大师非常关注文学,甚至有许多科学家也“越俎代庖”地跨领域来论述文学问题,有的甚至直接做起了文学批评。例如弗洛伊德对陀斯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研究,拉康对艾伦·坡的研究,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的研究,本雅明对波德莱尔的研究,萨特干脆自己写了大量小说。
的确,这是一个技术时代,人们在大多数时候只是工作的机器。我们上大学,要考计算机、英语等级证书,这些证书有什么用呢?它唯一的用处是可以证明我们的“实用性”,或者直白点说它是我们成为“机器”的合格标签。
对一个外资企业来说,一个拥有英语六级证书的人可能比只有四级证书的人更加能干;那些在流水线上作业的人们,对工厂来说他们也许首先是一些生产者,是为了生产这个目的而存在的人,他们是劳动力要素。总的说来,人总是倾向于被当成实现某个外在目的的工具,因此而处于被役使状态。
这种役使,有的时候是来自于他者。例如,工人是工厂企业赖以产生利润的工具。
大多数时候人的社会角色、名称标识正是因为这种工具性,比如农民、律师、医生、保姆等等。但很多时候,这种役使来自自我,人因为欲望而被驱遣,像对金钱、财富的欲壑难平。
一个仅仅为了金钱而奔波的人,常常有一种为了自己而活着的假象,但实际上是把自己当成了赚钱的工具,成了金钱的奴隶。 但是,人的本性并非如此,人在本性上是渴望自己成为目的,也即是说他希望自己就是目的本身,不做任何其他目的的工具,不为身外之物所役,事实上人类也只有在这种状态时才是真正自由的。
所以,经典哲学家曾设想,人类社会只有在某个物质文明到了“按需分配”的时代,才能真正脱离物役以及物欲。在那个阶段,人类不再为物质匮乏、多寡而忧心忡忡,甚至不用再为物质而劳动。
人类的活动以自己的爱好为基准,以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而且每个人的个性发展也以尊重其他人的个性发展为前提———也就是说,任何人个性的全面发展都不以剥削、压抑别人为基础,而是以别人也同样发展了的个性为基础。到这个时候,人类就真正进入了自由王国。
不过这是理想的状态,现实并非如此,而且常常是相反。因此,现实中的人类需要另外的东西来支撑。
这个支撑点在哪里呢?许多哲学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审美———想像世界的自由王国。审美地、诗意地栖居着的人,是摆脱了现实世界功利逻辑掌控的人,他漫无目的地游走在文学艺术的王国里,只是为了自己的趣味而活,因而这时他是一个自由的人。
从这个角度说,文学艺术其实是“无用”的:它给我们提供的只是幻想的自由、精神的自由、无功利的自由,而不是现实的有目的性的行为自由;它是一种理想的精神境界,而不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境遇;它是无形的精神愉悦,而不是现实的物质享受,甚至在某些时候它和某些物质享受还是对立的。就此,对于一个实用主义者来说,它可以说是“无用的”。
关于这一点,周作人有这样的说法:“泛称人生派的艺术,我当然是没有什么反对,但是普通所谓人生派是主张‘为人生的艺术’的,对于这个我却略有一点意见。‘为艺术的艺术’将艺术与人生分离,并且将人生附属于艺术,至于如王尔德的提倡人生之艺术化,固然不很妥当;‘为人生的艺术’以艺术附属于人生,将艺术当作改造生活的工具而非终极,也何尝不把艺术与人生分离呢?我以为艺术当然是人生的,因为他本是我们感情生活的表现,叫他怎能与人生分离?‘为人生’———于人生有实利,当然也是艺术本有的一种作用,但并非唯一的职务。
总之,艺术是独立的,却又原来是人性的,所以既不必使它脱离人生,又不必使它服侍人生,只任它成为浑然的人生的艺术便好了。‘为艺术’派以个人为主人,表现情思而成艺术,即为其生活之一部,初不为福利他人而作,而他人接触这艺术,得到一种共鸣与感兴,使其精神生活充实而丰富,又即以为实生活的基本;这是人生的艺术的要点,有独立的艺术美与无形的功利。
我所说的蔷薇地丁的种作,便如此。有些人种花聊以消遣,有些人种花志在卖钱;真种花者以种花为其生活,而花亦未尝不美,未尝于人无益。”
周作人蔷薇花的比喻很有意思,花原是无用之物,但是,“未尝与人无益”,真正的艺术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东西,“独立的艺术美”加上“无形的功利”,初不为福利他人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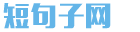 短句子网
短句子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