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求20篇余秋雨散文中的好句
1.余秋雨·笛声何处 [余秋雨] 2.余秋雨:出走十五年 [余秋雨] 3.余秋雨自传:借我一生 [余秋雨] 4.中国之旅: 跟随余秋雨的脚步 [余秋雨] 5.余秋雨文集 [余秋雨] 6.可怜的正本 [余秋雨] 7.狼山脚下 [余秋雨] 8.文化苦旅 [余秋雨] 9.江南小镇 [余秋雨] 10.寂寞天柱山 [余秋雨] 11.苏东坡突围 [余秋雨] 12.信客 [余秋雨] 13.关于友情 [余秋雨] 14.长者 [余秋雨] 15.上海人 [余秋雨] 16.中年当家的滋味 [余秋雨] 17.风雨天一阁 [余秋雨] 18.青年人的阅读 [余秋雨] 19.霜冷长河 [余秋雨] 20.关于名誉 [余秋雨] 21.抱愧山西 [余秋雨] 22.洞庭一角 [余秋雨] 23.流放者的土地 [余秋雨] 24.莫高窟 [余秋雨] 25.柳侯祠 [余秋雨] 26.千年庭院 [余秋雨] 27.十万进士 [余秋雨] 28.西湖梦 [余秋雨] 29.乡关何处 [余秋雨] 30.遥远的绝响 [余秋雨] 31.一个王朝的背影 [余秋雨] 32.这里真安静 [余秋雨] 33.道士塔 [余秋雨] 34.酒公墓 [余秋雨] 35.庙宇 [余秋雨] 36.阳关雪 [余秋雨] 37.夜航船 [余秋雨] 38.贵池傩 [余秋雨] 39.书海茫茫 [余秋雨] 40.小人 [余秋雨] 41.青云谱随想 [余秋雨] 42.余秋雨与批评者对话 [余秋雨] 43.余秋雨、余杰之两余之争 [余秋雨、余杰等] 将说得准的事情告诉学生, 将说不准的事情交给科研, 将说不清的事情写进散文。
什么是蒙昧和野蛮,什么是它们的对手——文明?每一次搏斗,文明都未必战胜,因此我们要远远近地为它呼喊几声。 ——《文明的碎片·题叙》 ●蒙昧—野蛮—文明,这实在是一个老而又老的话题。
人类专家常常把它们作为人类早期演进的三大阶段,那么,我们当然早已进入文明,而且千万年下来,早已进入一种充分成熟的文明。我们的一切举止行为,好像应该都有一些心照不宣的公认前提。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蒙昧和野蛮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时时滋生。它们理所当然在把嘲谑和消解文明作为自己生存本能。
没想到文明对此毫无警觉,它太相信那个所谓心照不宣的公认前提,对周围的世界仍然一往情深。 ——《文明的碎片·题叙》 ●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把并不存在的文明前提当作存在。
文明的伤心处,不在于与蒙昧和野蛮的搏斗中伤痕累累,而在于蒙昧和野蛮错看成文明。 ——《文明的碎片·题叙》 ●消解文明的日常理由往往要比建立文明的理由充分。
这便决定,文明的传播是一个艰难困苦甚至是忍辱负重的过程。 ——《文明的碎片·题叙》 ●社会上万事万物各自的理由组合不成文明。
文明是对琐碎实利的超越,是对各个自圆其说的角落的总体协调,是对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基元性原则的普及,是对处于日常迷顿状态的人们的提醒。然而,这种超越、协调、普及、提醒都是软性的,非常容易被消解。
——《文明的碎片·题叙》 ●剥除文明的最后结果,就是容忍邪恶,无视暴虐,文明被撕成了碎片,任人搓捏和踩踏。人类历史上一切由人类自己造成的悲剧,大半由此而生。
——《文明的碎片·题叙》 ●最强大的哲人也无力宣称,他可以从整体上营造一种文明。人们能做的极致,也就是为社会和历史提供一些约定俗成的起码前提。
这些前提是人性的公理、道义的基石、文化的共识、理性的入门,也就是世俗社会所谓的常情常理。没有这一切,社会无以构成,人类无以自存,因此,所有良知未泯的文化人都应该来参与构建文明前提的事业。
——《文明的碎片·题叙》 ●文明的火种会不会在漠然者的心头重新点燃?文明的前提会不会使他们恍然收起振振有词的各自理由?具体来说,我们的一切文化行为会不会在人们心中产生真正的积极反应? ——《文明的碎片·题叙》 ●称为文明古国,至少说明在我们国家文明和蒙昧、野蛮的交战由来已久。交战的双方倒下前最终都面对后代,因此我们身上密藏着它们的无数遗嘱。
——《文明的碎片·题叙》 ●我曾隐隐地感觉到,我们的故乡也许是一个曾经很成器的地方,它的“大器”不知碎于何时,碎得如此透彻,像轰然山崩,也像渐然家倾。为了不使后代看到这种痕迹,所有碎片的残梦被湖水淹没……区区如我,毕生能做的,至多也是一枚带有某种文明光泽的碎片罢了。
没有资格跻身某个遗址等待挖掘,没有资格装点某种碑亭承受供奉,只是在与蒙昧和野蛮的搏斗中碎得于心无愧。无法躲藏于家乡的湖底,无法奔跑于家乡的湖面。
那就陈之于异乡的街市吧,即便被人踢来踢去,也能铿然有声。偶尔有哪个路人注意到这种声音了,那就顺便让他看看一小片洁白和明亮。
——《乡关何处》 ●蒙昧往往有朴实的外表,野蛮常常有勇敢的假相,从历史眼光来看,野蛮是人们逃开蒙昧的必由阶段,相对于蒙昧是一种进步;但是,野蛮又绝不愿意就范于文明,它会回过身去与蒙昧结盟,一起来对抗文明:外表朴实的对手和外表勇敢的对手,前者是无知到无可理喻,后者是强蛮到无可理喻。更麻烦的是,这些对手很可能与已有的文明成果混成一体,甚至还会悄悄地潜入人们的心底,使我们寻找它们的时候常常寻找到自己的父辈,自己的故乡,自己的历史。
——《乡关何处》 ●文明易碎,文明的碎片有可能被修补,有可能无法修补,然而即便是无法修补的碎片,也会保存着高贵的光彩,永久地让人想像。能这样,也就够了。
——《乡关何处》 ●文明可能产生于野蛮,却绝。
2.文化苦旅好句好段评论
重读《道士塔》 一 因为要上《道士塔》的原因,上午上了一节课听了一节课后,不得不坐在办公室里,和余秋雨再做一次迫不得已的交流。
十年前读余的《文化苦旅》时,《道士塔》的印象还是挺深的。作者极尽嘲讽挖苦之能事,对整个民族的悲剧的怜悯痛恨之心,以及余氏特有的看似厚重的文化情绪,当时很是触动。
那时,余秋雨的真实面目我还不是看的很清楚,当他摆起一副渊博厚重的姿势之后,后生小子还真有点爱不释手。那时,一本精装的《文化苦旅》》要二十多元,但我还是忍痛买了,后来余出一本,我买一本,《霜冷长河》《千年一叹》《秋千架》《山居笔记》等等,一路买来,颇花费了我大量的银子。
可惜的是,现在这些书一本本的躺在我的书架上,我再也懒得碰。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是越来越厌恶余秋雨,偌大一个中国,文人无数,余是典型的文人无行,面目可憎;另一方面,这些书都以文化精品的面目出现的,可是现在读他,只觉得暗藏在字里行间的只是摆谱而已,已经读不出半点的文化了。
《道士塔》这篇文章,以前《读者》杂志刊登过,后来收在《文化苦旅》里的《病梅记》《都江堰》《白发苏州》等等好象也都在《读者》上亮过相,余书现在大行于天下,我想和《读者》的一再推崇是分不开的。道士王圆渌的所作所为,后来也在其他的地方见过记载,没有余说的那么糟。
一个穷道士而已,把持敦煌不是他的错,也只是当时的体制,敦煌所在,大漠戈壁,漫漫黄沙,整日面对可怖的石像,腐烂的经书,一般的官员谁愿意去,而且当时,敦煌的卷宗和石像也不像现在是什么什么文化的象征,这些东西后来一批一批被外国人买走、偷走,被他们研究之后才被国人重视,才被称之为“文化”。王道士的所作所为,比起满清王朝北洋军政的租借卖地屠杀国人丧权辱国的行径,只是个小样而已。
可是余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泻”真是有点莫须有。在文章中,余一再写王道士的“卑微、渺小、愚昧”,一再对他揶揄嘲讽挖苦,一再表示对他愤恨,而对来买经卷、偷经卷的斯坦因、伯希和等等描写,作者是一再的写他们的不远万里、风餐露宿、倾家荡产,一再的称他们为学者为专家,一再的写他们对文化研究的热爱。
不经意间,余的用心和骨子里那点货色动已经显山露水了,斯坦因、伯希和等等能算学者专家吗?他们是冒险家,是强盗,他们只是和义律和瓦德西一样的掠夺者。余不把他所谓的满腔怒火向这些人倾泻,而把种种无端的罪归于王道士一人,不知道是什么情结在使然。
这样的文笔做派,这样貌似爱国、爱文化的姿态,这样莫名其妙的情绪,在余的其他书籍里都是一样的,可惜的是,许多人视而不见,以至余书大行特行,为余赚足了银子。 二 敦煌的卷子我在《书法》杂志上读过一些,唐代僧人开始抄的经书也确实令现代任何一个有名的大书法家叹为观止。
一代代的无籍可考的僧人无日无夜的抄录经书,《金刚经》《莲花经》《心经》《观音经》等等,一本本的抄,几千本几万本的抄录,一代代的积压沉淀,一代代的无名的僧人由少抄到老,然后死掉,然后又一代代的僧人接着干,这样的日积月累,就形成了敦煌蔚为大观的经卷,也成就了现在无数学者为之殚精竭虑的敦煌文化。 从1902年王道士把敦煌一个藏经洞的几册经卷送到甘肃学台叶昌炽开始,到1930年近代学者陈寅恪首先提出,敦煌渐成一门学问,称之为敦煌学。
甘肃河西这个地方,原来是有名的河套草原,牛肥马壮,隋以后开始沙化,至唐以后,几个和尚来到敦煌,见此处的石材不错,就挖了几个石窟,躲在里面研究佛教大义。佛家和儒家道家的修行研究形式是不一样的,佛家的修行方式是念经抄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中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于此经受持书写读诵,则为如来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见是人,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 “书写读诵”即能成就这“无量无边功德”,于是抄经读经成了所有僧人的日常作业。
有的僧人一生抄经书无数,至死也没弄明白“明净台、菩提树”,但却积累了书法学、文字学、经学的种种繁荣的端倪。有一段时间,我曾认真的临写过敦煌的明代一无名僧人抄录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这个和尚,穷一生之力抄录《金刚般若波罗蜜经》4万多册,虽没有成佛,但书体的老道精妙,笔势的美妍流畅,已是书之神品。
也难怪敦煌学能够引起国际学界的注意。 三 敦煌学现在的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敦煌遗书、敦煌石窟、敦煌史迹。
当年王道士一块两块的银圆买掉的经卷,已经成了不列颠博物馆的藏品,一册经卷在拍卖场上几百万几千万美元的记录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若是王道士地下有知,不知现在做何感想。王道士是个可怜的道士,生前用经卷换几个铜板以求生计,没有什么民族文化、佛教文化、敦煌文化的概念,余把文物遗失的罪归在他身上,既是王道士的悲剧,也是余秋雨自己的悲剧。
余秋雨作为一个流行的作家,写着流行的文章,论着流行的话题,说着流行的声调,用流行吸引大众的眼球,以买文赚钱卖房卖车住高楼,这本身是没有错的。可惜的是,这个流行的作家定位不够,他偏偏以一个文化人甚至以文化。
3.求余秋雨散文中好句
作者:余秋雨 来源:不详 我一直想写写“江南小镇”这个题目,但又难于下笔。
江南小镇太多了,真正值得写的是哪几个呢?一一拆散了看,哪一个都构不成一种独立的历史名胜,能说的话并不太多;然而如果把它们全躲开了,那就是躲开了一种再亲昵不过的人文文化,躲开了一种把自然与人情搭建得无比巧妙的生态环境,躲开了无数中国人心底的思念与企盼,躲开了人生苦旅的起点和终点,实在是不应该的。 我到过的江南小镇很多,闭眼就能想见,穿镇而过的狭窄河道,一座座雕刻精致的石桥,傍河而筑的民居,民居楼板底下就是水,石阶的埠头从楼板下一级级伸出来,女人正在埠头上浣洗,而离他们只有几尺远的乌蓬船上正升起一缕白白的炊烟,炊烟穿过桥洞飘到对岸,对岸河边有又低又宽的石栏,可坐可躺,几位老人满脸宁静地坐在那里看着过往船只比之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河边由吊脚楼组成的小镇,江南小镇少了那种浑朴奇险,多了一点畅达平稳。
它们的前边没有险滩,后边没有荒漠,因此虽然幽僻却谈不上什厶气势;它们大多有很有一些年代了,但始终比较滋润的生活方式并没有让它们保留下多少废墟和遗迹,因此也听不出多少历史的浩叹;它们当然有过升沈荣辱,但实在也未曾摆出过太堂皇的场面,因此也不容易产生类似于朱雀桥、乌衣巷的沧桑之慨。总之,它们的历史路程和现实风貌都显得平实而耐久,狭窄而悠久,就像经纬着它们的条条石板街道。
堂皇转眼凋零,喧腾是短命的别名。想来想去,没有比江南小镇更足以成为一种淡泊而安定的生活表征的了。
中国文人中很有一批人在入世受挫之后逃于佛、道,但真正投身寺庙道观的并不太多,而结庐荒山、独钓寒江毕竟会带来基本生活上的一系列麻烦。“大隐隐于市”,最佳的隐潜方式莫过于躲在江南小镇之中了。
与显赫对峙的是常态,与官场对峙的是平民,比山林间的蓑草茂树更有隐蔽力的是消失在某个小镇的平民百姓的常态生活中。山林间的隐蔽还保留和标榜着一种孤傲,而孤傲的隐蔽终究是不诚恳的;小镇街市间的隐蔽不仅不必故意地折磨和摧残生命,反而可以把日子过得十分舒适,让生命熨贴在既清静又方便的角落,几乎能gou4把自身由外到里溶化掉,因此也就成了隐蔽的最高形态。
说隐蔽也许过于狭隘了,反正在我心目中,小桥流水人家,莼鲈之思,都是一种宗教性的人生哲学的生态意象。 在庸常的忙碌中很容易把这种人生哲学淡忘,但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它就会产生一种莫名的诱惑而让人渴念。
记得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期,我父亲被无由关押,尚未结婚的叔叔在安徽含冤自尽,我作为长子,20来岁,如何掌持这个八口之家呢?我所在的大学也是日夜风起云涌,既不得安生又逃避不开,只得让刚刚初中毕业的大弟弟出海捕鱼,贴补家用。大弟弟每隔多少天后上岸总是先与我连系,怯生生地询问家里情况有无继续恶化,然后才回家。
家,家人还在,家的四壁还在,但在那年月好像是完全暴露在露天中,时时准备遭受风雨的袭击和路人的轰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些大学毕业生又接到指令必须到军垦农场继续改造,去时先在吴江县松陵镇整训一段时间。
那些天,天天排队出操点名,接受长篇训话,一律睡地铺而夥食又极其恶劣,大家内心明白,整训完以后就会立即把我们抛向一个污泥,沼泽和汗臭相拌和的天地,而且绝无回归的时日。我们的地铺打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从西边墙板的袷缝中偷眼望去,那里有一个安静的院落,小小一间屋子面对着河流,屋里进去的显然是一对新婚夫妻,与我们差不多年龄。
他们是这个镇上最普通的居民,大概是哪家小店的营业员或会计罢,清闲得很,只要你望过去,他们总在,不紧不慢地做着一天生活所必需,却又纯然属于自己的事情,时不时有几句不冷也不热的对话,莞尔一笑。夫妻俩都头面干净,意态安详。
当时我和我的同伴实在被这种最正常的小镇生活震动了。这里当然也遇到了文化大革命,但毕竟是小镇,又兼民风柔婉,闹不出多大的事,折腾了一两下也就烟消云散,恢复成寻常生态。
也许这个镇里也有个把“李国香”之类,反正这对新婚夫妻不是,也不是受李国香们注意的人物。咳,这样活着真好!这批筋疲力尽又不知前途的大学毕业生们向壁缝投之以最殷切的艳羡。
我当时曾警觉,自己的壮气和锐气都到哪儿去了,何以20来岁便产生如此暮气的归隐之想?是的,那年在恶风狂浪中偷看一眼江南小镇的生活,我在人生憬悟上一步走向了成年。 我躺在垫着稻草的地铺上,默想着100多年前英国学者托马斯·德·昆西(T .De Quincey) 写的一篇著名论文:《论〈麦克白〉中的敲门声》。
昆西说,在莎士比亚笔下,麦克白及其夫人借助于黑夜在城堡中杀人篡权,突然,城堡中响起了敲门声。这敲门声使麦克白夫妇恐慌万状,也历来使所有的观众感到惊心动魄。
原因何在?昆西思考了很多年,结论是:清晨敲门,是正常生活的象征,它足以反衬出黑夜中魔性和兽性的可怖,它又宣告着一种合乎人性的正常生活正有待于重建,而正是这种反差让人由衷震撼。在那些黑夜里,我躺在地铺上,听到了江南小镇的敲门声,笃笃笃,轻轻的,隐。
4.余秋雨道士塔读书笔记
道士塔——荣耀与耻辱的见证 《道士塔》是余秋雨的一篇“文化散文”,2000年入选人教版高中《语文》新教材第三册第三单元。
这篇散文形象地深省并揭示了酿成中国古代灿烂文化悲剧的社会根源。作者对中华民族文明史的反思,表现了作者强烈的忧患意识,读起来让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扼腕。
文章之所以有如此大的魅力,跟作者成功地运用对比手法是密不可分的。 文章由小到大、由实到虚运用了四组对比,深刻地展示了近代中国由于愚昧和落后而带来的一场不可避免的民族文化悲剧。
艺术宫殿与农家宅院 文章开头由描写莫高窟的僧侣圆寂塔入笔:“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 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
作者以简短的语句、冷色的笔调将当年的这些“民族文化守护者”的形象置于大西北的漠漠黄沙之中,使得“夕阳西下,朔风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这里的“悲凉”就定下了文章“反思”的基调。
莫高窟的一幅幅生动的壁画,所藏的价值连城的书画,不仅是宗教艺术,而且是历史的画卷,是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 可是无知的王圆箓却将这样的艺术宫殿当成了农家宅院!作者用想象的笔触生动地写道,他“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
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 他觉得,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中座的塑雕“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美的浅笑有点尴尬”,于是几个铁锤,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成了泥巴”。
试问,谁读到这样形象的对比不从心底油然而生一阵“悲凉”?!更幽默的让人心痛的是这么一段:“‘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 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 遗产保护与国宝流失 如何对待文化遗产?作者分列对写。
一边是中国,“中国官员也不是都没有学问,他们也已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翻动出土经卷,推测着书写朝代了”,“他们文雅地摸着胡须,吩咐手下:‘什么时候,叫那个道士再送几件来!’已得的几件,包装一下,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品”。 是的,他们看重的是个人的、眼前的名利,至于国家的、民族的过去与未来,那是口号而已!再看另一边,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正“不远万里,风餐露宿”地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变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他们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做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刚刚打开的洞窟赶来。
作者在这里的对比中留下了经典的“烟气”意象:“他们在沙漠里燃起了股股炊烟,而中国官员的客厅里,也正茶香缕缕。” “小丑演员”与“整幕话剧” 显然,文章的主旨并不是为了批判那个“历史的罪人”王圆箓。
王圆箓,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作者引来对比的是一个小丑演员与一整幕话剧的对比———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
其实,这个小丑王圆箓只是一个符号而已。在“茶香缕缕”的“天朝大国”里,“目光呆滞”的无知躯体实在太多,其中由谁来“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这就是这组对比的价值。
作者在运用对比时没有忘记将其具体化和形象化:“1905年10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携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又来,仍用一点银元换去了五大箱、六百多卷经卷……”道士要的只是一笔最轻松的小买卖,“就像用两枚针换一只鸡,一颗纽扣换一篮青菜”,洋人把我们的国宝运到伦敦,运到巴黎,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我们的王道士却“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 理想与现实 扼腕的同时,余秋雨先生想到了“假如”。 假如让作者生在那时,又恰恰在西方人就要将国宝运走的刹那站在他们面前———“然后怎么办呢?”爱国的理想是好的,可是作者在这里向我们设置了一个艺术创作里的“未知结构”,提出了一个“两难悖反”:衷心希望留下,留下的结果是“送京”,“送京”的命运是“零零落落”;万分痛心“掠走”,“掠走”的命运是至今仍完好无损地“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被拦住的车队,究竟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然后大哭一场”。
作者的思想感情是复杂的,压抑、悲痛交织在一起。 “道士塔”早已淹埋在历史的风尘中,但余秋雨“理想与现实”的对比却还在我们面前回荡。
面对过去,我们能挺直腰杆批判无知的“王道士”,可是今天,不是仍然有人把祖宗的文化遗产当作“大盘菜”毫不吝惜地大吃大嚼吗?“住手!”谁在心底痛苦地呼喊?。
5.文化苦旅好句好段评论
重读《道士塔》 一 因为要上《道士塔》的原因,上午上了一节课听了一节课后,不得不坐在办公室里,和余秋雨再做一次迫不得已的交流。
十年前读余的《文化苦旅》时,《道士塔》的印象还是挺深的。作者极尽嘲讽挖苦之能事,对整个民族的悲剧的怜悯痛恨之心,以及余氏特有的看似厚重的文化情绪,当时很是触动。
那时,余秋雨的真实面目我还不是看的很清楚,当他摆起一副渊博厚重的姿势之后,后生小子还真有点爱不释手。那时,一本精装的《文化苦旅》》要二十多元,但我还是忍痛买了,后来余出一本,我买一本,《霜冷长河》《千年一叹》《秋千架》《山居笔记》等等,一路买来,颇花费了我大量的银子。
可惜的是,现在这些书一本本的躺在我的书架上,我再也懒得碰。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是越来越厌恶余秋雨,偌大一个中国,文人无数,余是典型的文人无行,面目可憎;另一方面,这些书都以文化精品的面目出现的,可是现在读他,只觉得暗藏在字里行间的只是摆谱而已,已经读不出半点的文化了。
《道士塔》这篇文章,以前《读者》杂志刊登过,后来收在《文化苦旅》里的《病梅记》《都江堰》《白发苏州》等等好象也都在《读者》上亮过相,余书现在大行于天下,我想和《读者》的一再推崇是分不开的。道士王圆渌的所作所为,后来也在其他的地方见过记载,没有余说的那么糟。
一个穷道士而已,把持敦煌不是他的错,也只是当时的体制,敦煌所在,大漠戈壁,漫漫黄沙,整日面对可怖的石像,腐烂的经书,一般的官员谁愿意去,而且当时,敦煌的卷宗和石像也不像现在是什么什么文化的象征,这些东西后来一批一批被外国人买走、偷走,被他们研究之后才被国人重视,才被称之为“文化”。王道士的所作所为,比起满清王朝北洋军政的租借卖地屠杀国人丧权辱国的行径,只是个小样而已。
可是余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泻”真是有点莫须有。在文章中,余一再写王道士的“卑微、渺小、愚昧”,一再对他揶揄嘲讽挖苦,一再表示对他愤恨,而对来买经卷、偷经卷的斯坦因、伯希和等等描写,作者是一再的写他们的不远万里、风餐露宿、倾家荡产,一再的称他们为学者为专家,一再的写他们对文化研究的热爱。
不经意间,余的用心和骨子里那点货色动已经显山露水了,斯坦因、伯希和等等能算学者专家吗?他们是冒险家,是强盗,他们只是和义律和瓦德西一样的掠夺者。余不把他所谓的满腔怒火向这些人倾泻,而把种种无端的罪归于王道士一人,不知道是什么情结在使然。
这样的文笔做派,这样貌似爱国、爱文化的姿态,这样莫名其妙的情绪,在余的其他书籍里都是一样的,可惜的是,许多人视而不见,以至余书大行特行,为余赚足了银子。 二 敦煌的卷子我在《书法》杂志上读过一些,唐代僧人开始抄的经书也确实令现代任何一个有名的大书法家叹为观止。
一代代的无籍可考的僧人无日无夜的抄录经书,《金刚经》《莲花经》《心经》《观音经》等等,一本本的抄,几千本几万本的抄录,一代代的积压沉淀,一代代的无名的僧人由少抄到老,然后死掉,然后又一代代的僧人接着干,这样的日积月累,就形成了敦煌蔚为大观的经卷,也成就了现在无数学者为之殚精竭虑的敦煌文化。 从1902年王道士把敦煌一个藏经洞的几册经卷送到甘肃学台叶昌炽开始,到1930年近代学者陈寅恪首先提出,敦煌渐成一门学问,称之为敦煌学。
甘肃河西这个地方,原来是有名的河套草原,牛肥马壮,隋以后开始沙化,至唐以后,几个和尚来到敦煌,见此处的石材不错,就挖了几个石窟,躲在里面研究佛教大义。佛家和儒家道家的修行研究形式是不一样的,佛家的修行方式是念经抄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中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于此经受持书写读诵,则为如来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见是人,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 “书写读诵”即能成就这“无量无边功德”,于是抄经读经成了所有僧人的日常作业。
有的僧人一生抄经书无数,至死也没弄明白“明净台、菩提树”,但却积累了书法学、文字学、经学的种种繁荣的端倪。有一段时间,我曾认真的临写过敦煌的明代一无名僧人抄录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这个和尚,穷一生之力抄录《金刚般若波罗蜜经》4万多册,虽没有成佛,但书体的老道精妙,笔势的美妍流畅,已是书之神品。
也难怪敦煌学能够引起国际学界的注意。 三 敦煌学现在的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敦煌遗书、敦煌石窟、敦煌史迹。
当年王道士一块两块的银圆买掉的经卷,已经成了不列颠博物馆的藏品,一册经卷在拍卖场上几百万几千万美元的记录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若是王道士地下有知,不知现在做何感想。王道士是个可怜的道士,生前用经卷换几个铜板以求生计,没有什么民族文化、佛教文化、敦煌文化的概念,余把文物遗失的罪归在他身上,既是王道士的悲剧,也是余秋雨自己的悲剧。
余秋雨作为一个流行的作家,写着流行的文章,论着流行的话题,说着流行的声调,用流行吸引大众的眼球,以买文赚钱卖房卖车住高楼,这本身是没有错的。可惜的是,这个流行的作家定位不够,他偏偏以一个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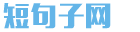 短句子网
短句子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