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汪曾祺作品里的好词好句有哪些
1、有的小说,是写农村的。对话是农民的语言,叙述却是知识分子的语言,叙述和对话脱节。
2、小说的语言是浸透了内容的,浸透了作者的思想的。我们有时看一篇小说,看了三行,就看不下去了,因为语言太粗糙。语言的粗糙就是内容的粗糙。
3、语言,是内在地运行着的。缺乏内在的运动,这样的语言就会没有生气,就会呆板。
4、好的语言都是平平常常的,人人能懂,并且也可能说得出来的语言--只是他没有说出来。
5、往往有这样的说法:这篇小说写得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6、我最近看了一个青年作家写的小说,小说用的是第一人称,小说中的“我”是一个才人小学的孩子,写的是“我”的一个同桌的女同学,这未尝不可。但是这个“我”对他的小同学的印象却是:“她长得很纤秀。”这是不可能的。小学生的语言里不可能有这个词。
7、人人心中所有,笔下所无。“红杏枝头春意闹”,“满宫明月梨花白”都是这样。“闹”字“白”字,有什么稀奇呢?然而,未经人道。
8、我想任何人的语言都是这样,每句话都是警句,那是会叫人受不了的。
9、不单是对话,就是叙述描写的语言,也要和所写的人物”靠”。
10、一个人精神好的时候往往会才华横溢,妙语如珠;倦疲的时候往往词不达意。
11、我的习惯是,打好腹稿。我写京剧剧本,一段唱词,二十来句,我是想得每一句都能背下来,才落笔的。
12、我们不能说这首曲子不错,就是旋律和节奏差一点;这张画画得不错,就是色彩和线条差一点。我们也不能说:这篇小说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
13、语言的奥秘,说穿了不过是长句与短句的搭配。
14、若我在临水照影里,想起你,若我在柳枝新绿前想起你,若我在一切无从说,说不好的美丽里想起你,我在那一切陶醉里,已非自醉,你可曾感受到,遥远的举杯致意。逝去的从容逝去,重温的依然重温,在沧桑的枝叶间,折取一朵明媚,簪进岁月肌里,许它疼痛又甜蜜,许它流去又流回,改头换面千千万,我认取你一如初见。
15、他(闻一多)在很年轻的时候,写过一篇《庄子》,说他的文字(即语言)已经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本身即是目的(大意)。我认为这是说得很对的。
2.汪曾祺作品里的好词好句10句
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
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
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
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来了一船瓜、一船颜色和欲望。一船是石头,比赛着棱角。也许——一船鸟,一船百合花。深巷卖杏花。骆驼。骆驼的铃声在柳烟中摇荡,鸭子叫,一只通红的蜻蜓。
3.汪曾祺散文/世纪文存好词好句
汪曾祺散文
作者:汪曾祺 著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5-1
ISBN:7020050344
字数:200000
印次:1
版次:1
纸张:胶版纸
定价:21 元
内容提要
中华散文,源远流长。数千年的散文创作,或抒情、或言志、成状景、或怀人……莫不反映出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们的思想情感。中华散文的这些优良传统在二十世纪以降的新文学那里,不仅得到了全面传承,且不断有所创新、有所发展。为了展示二十世纪以来中华散文的创作业绩,编者在新世纪之初即编辑出版过“中华散文珍藏本”凡三十种。时光五载已过,编者又在此基础上精编出这套“中华散文插图珍藏版”十六种。经再次遴选,本丛书不仅每册新增加五万余字,而且每册还辅以反映其人生历程的珍贵照片若干幅。可谓美文与华照相得益彰,既是伴君品味欣赏之佳作,又为珍藏馈赠之上品。
作者简介
汪曾祺(1920-1997),现当代作家。江苏高邮人。1939年考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深受教写作课的沈从文的影响。1940年开始发表小说。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北京剧协理事,在海内外出版专著全集30余部,代表作有小说《受戒》、京剧剧本《范进中举》、《沙家浜》(主要编者之一)。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
编辑推荐
美文与华照相得益彰,既是伴君欣赏之佳作,又为珍藏馈赠之上品。
目录
我的家乡
文游台
观音寺
午门忆旧
一辈古人
吴大和尚和七拳半
新校舍
泡茶馆
跑警报
自得其乐
自报家门
随遇而安
多年父子成兄弟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金岳霖先生
老舍先生
国子监
钓鱼台
水母
城隍·土地·灶王爷
老不闲抄
胡同文化
我是一个中国人
故乡的食物
吃食和文学
宋朝人的吃喝
葵·薤
五味
寻常茶话
食豆饮水斋闲笔
韭菜花
花
果园杂记
葡萄月令
翠湖心影
昆明的雨
湘行二记
泰山片石
北京的秋花
林肯的鼻子
美国短简
香港的鸟
谈风格
谈谈风俗画
“揉面”
《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
关于《受戒》
4.汪曾祺散文好词好句
我曾经在一次讲话中说到归有光善于以清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事.这个意思其实古人早就说过.黄梨洲<;文案>;卷三<;张节母叶孺人墓志铭>;云: "予读震川之文为女妇者,一往情深,每以一,二细事见之,使人欲涕,盖古今来事无巨细,惟此可歌可泣之精神长留天壤."
"归有光的名文有<;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寒花葬志>;等篇.我受到影响的也只是这几篇.归有光在思想上是正统派,我对他的那些谈学论道的大文实在不感兴趣.我曾想:一个思想迂腐的正统派,怎么能写出那样富于人情味的优美的抒情散文呢?这个问题我一直还没有想明白.
"他是真正做到 "无意为文",写得象谈家常话似的.他的结构 "随事曲折".若无结构.他的语言更接近口语,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衔接处若无痕迹.他的<;项脊轩志>;的结尾: 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平淡中包含几许惨恻,悠然不尽,是中国古文里的一个有名的结尾,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趋舍不同,静躁异趣,杜甫不能为李白的飘逸,李白也不能为杜甫的沉郁.苏东坡的词宜关西大汉执铁绰板唱:"大江东去",柳耆卿的词宜十三,四女郎持红牙板唱 "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中国的词可分豪放和婉约两派,其他文体大体也可以这样划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因为什么,豪放派占了上风,茅盾同志曾经很感慨地说:现在很少人写婉约的文章了." 十年浩劫,没有人提起风格这个词,我在 "样板团"工作过, 江青规定: "要写大江东去,不要小桥流水."我是个只会写小桥流水的人也只好唱了十年空空洞洞的豪言壮语. _____以上摘自 <;谈风格>
"<;边城>;激怒了一些理论批评家,文学史家,因为沈从文没有按照他们的要求,他们规定的模式写作."
"第一条罪名是<;边城>;没有写阶级斗争,掏空了人物的阶级属性" 针对这样的批评,沈从文作了挑战性的答复: "你们多知道要作品有"思想",有"血"有 "泪",且要求一个作品具体表现这些东西到故事发展上,人物语言,甚至一本书的封面上,目录上.你们要的事多容易办,可是我不能给你们这个,我存心放弃你们。。"
"第二条罪名,与第一条相关联,是说<;边城>;写的是一个世外桃源,脱离现实生活, <;迷城>;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的? <;边城>;有没有把现实生活理想化?这是个非常叫人困惑的问题.
"为什么这个小说叫边城?这是个值得想一想的问题. <;边城>;不只是个地理概念,意思不是说这是个边地的小城,这同时是个时间概念,文化概念.
"<;边城>;是大城市的对立面,这是中国"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种事情."
"边城是一个怀旧的作品,一种带着痛惜情绪的怀旧, 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隐伏着作者很深的悲剧感.可以说,边城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边城>;的生活是真实的,同时又是理想化了的.这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现实.
"为什么要浪漫主义?为什么要理想化? 因为想留住一点美好的,永恒的东西,让它长在,并且常新.以利于后人."
5.汪曾祺作品集句子赏析
汪曾祺的散文写风俗,谈文化,忆旧闻,述掌故,寄乡情,花鸟鱼虫,瓜果食物,无所不涉。
在《夏天的昆虫》中,他向读者介绍了蝈蝈、蝉、蜻蜓、螳螂的品种、习性和孩童捕捉昆虫的情形。如他说:“叫蛐子(蝈蝈的俗称)是可以吃的。
得是三尾的,腹zd大多子。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
味极似虾”。说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胶捉蝉。
作者小时候用蜘蛛网捉蝉"选一根结实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络满了蜘蛛网,很黏。瞅准了一只蝉,轻轻一捂,蝉的翅膀就被粘住了。
"读到此处,不觉会心一笑,好像说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
如《吃食的文学》和《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
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答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6.《汪曾祺自选集》好词好句好段
她挎着一篮子荸荠回去了,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了一串脚印。
明海看着她的脚印,傻了。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
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
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 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你说话呀!” 明子说:“嗯。”
“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 明子大声地说:“要!” “你喊什么!” 明子小小声说:“要——!” “快点划!” 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芦花才吐新穗。
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
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
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 一九八○年八月十二日,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 【写作】 后记:我也愿意谢谢新的生活,新的人物。
但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
但是我现在还不能。对于现实生活,我的感情是相当浮躁的。
这三篇也是短小说。《詹大胖子》和《茶干》有人物无故事,《幽冥钟》则几乎连人物也没有,只有一点感情。
这样的小说打破了小说和散文的界限,简直近似随笔。结构尤其随便,想到什么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我这样做事有意的(也是苦心经营的)。我要对“小说”这个概念进行一次冲决: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小说要真诚,不能耍花招。
小说当然要讲技巧,但是:修辞立其诚。(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夜) 我说:“你写之前得先想想,想清楚再写呀。
李笠翁说,要袖手于前,才能疾书于后哪!”(《云致秋行状》) 他始终记住老师沈从文对他的告诫:“千万不要冷嘲”。赞成沈从文的“最反对愤世嫉俗,玩世不恭”。
欣赏沈从文“总是用一种善意的、含情的微笑来看待这个世界的一切”。“不意愿展示伤疤,以呈英雄豪气;不意愿发小我激情,以臧否纷繁的大千世界。”
关注着世人,思考他们,同情他们,爱他们。他十分崇尚沈从文对生活、对人、对山河草木都充满感情,对什么都爱着,用一颗蔼然之心爱着。
(徐卓人《永远的汪曾祺》) 【汪曾祺】 重印后记: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挺可爱的人,因为我比较真诚。重读一些我的作品,发现:我是很悲哀的。
我觉得,悲哀是美的。当然,在我的作品里可以发现对生活的欣喜。
弘一法师临终的偈语:“悲欣交集”,我觉得,我对这样的心境,是可以领悟的。---------------------------------- 汪曾祺办事处人,不靠作派,不使技巧,不玩花活,就凭一副真面孔,一个真性情。
对谁都谦虚有礼,朴素实在。真谈起问题来,你才发现此人学问有真知卓见,写作有独到之功,使你敬而不生畏,爱而不生烦。
(邓友梅《漫忆汪曾祺》)----------------------------------- 汪曾祺既得人生之精义,于是他也就具备了坚韧的心理承受力。他的这种状况 外在的表露常常被人说为“淡泊”。
其实这“淡泊”是对世俗的一种涵化,是他对现世清醒到极至的一种反悖。他在赠我的《当代散文大系·汪曾祺》扉页上题词:“我并不在葫芦里,卓人以为如何?”因为那本书的封面上画着一个葫芦,葫芦里蜷着一个打着瞌充的老头子!他自己也写道:“我的感情是真实的。
一些写我的文章每每爱写我如何恬淡、潇洒、飘逸,我简直成了半仙!你们如果跟我接触得较多,便知道我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汪曾祺不擅以大喜大悲怪诞离奇制造效果,却以一种轻声的叹息慑服了人。
人世间的悲哀,可怜,萎琐,一切乏人兴趣甚至让人鄙薄的行为作派,一旦到了他的笔下,就顿生出脉脉的怜情和绵绵的酸涩,就变成了人类共同的苦恼和弱点的暗示,变成了人性涨落的一种提示。汪曾祺当然是怀着巨大的同情心去进行这种暗示与提示的,他完全是沉浸在人物里表现人物的。
他习惯于把人世间的痛苦嚼碎了,咽到肚里,而后缓缓化解成那种味,这是一种微甜、微苦、微涩、微酸的五味相融的味,是一种经久永恒的味,痛恨,但不咬牙切齿;欢乐,但不得意忘形。他习惯于勇敢地承受世事,然后涵化丑,融化恶,这使他与他的文学具有了独特的人格力量。
我忽然想起汪曾祺写的《沈从文的寂寞》,他感叹沈先生重造民族品德的思想多年来不被理解。他引用沈先生的话:“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学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
“寄意寒星荃不察。”汪曾祺说,沈先生不能不感到寂寞;而他自己的散文里一再提到屈原,也不是偶然的。
最可敬是汪曾祺与他所观察以及所表现的人物始终站在同一水平线上,尊重他笔底的人物,将他们当成自己的朋友。他始终记住老师沈从文对他的告诫:“千万不要冷嘲”。
赞成沈从文的“最反对愤世嫉俗,玩世不恭”。欣赏沈从文“总是用一种善意的、含情的微笑来看待这个世界的一切”。
7.小学生汪曾祺读本好词好句
新校舍大门东边的围墙是“民主墙”。墙上贴满了各色各样的壁报,左、中、右都有。有时也有激烈的论战。有一次三青团办的壁报有一篇宣传国民党观点的文章,另一张群社编的壁报上很快就贴出一篇反驳的文章,批评三青团壁报上的文章是“咬着尾巴兜圈子”。这批评很尖刻,也很形象。“咬着尾巴兜圈子”是狗。
图书馆的管理员是一个妙人。他没有准确的上下班时间。有时我们去得早了,他还没有来,门没有开,我们就在外面等着。他来了,谁也不理,开了门,走进阅览室,把壁上一个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拉拉”一拨,拨到八点,这就上班了,开始借书。这个图书馆的藏书室在楼上。楼板上挖出一个长方形的洞,从洞里用绳子吊下一个长方形的木盘。借书人开好借书单——管理员把借书单叫做“飞子”,昆明人把一切不大的纸片都叫做“飞子”,买米的发票、包裹单、汽车票,都叫做“飞子”,——这位管理员看一看,放在木盘里,一拽旁边的铃铛,“当啷啷”,木盘就从洞里吊上去了。——上面大概有个滑车。不一会,上面拽一下铃铛,木盘又系了下来,你要的书来了。
她问了我一些问题。其中一个是,为什么我的小说里总有水?即使没有水,也有水的感觉"
祖父年轻时建造的几进,是灰青色与褐色的。我自小养育于这种安定与寂寞里。报春花开放在这种背景前是好的。它不至被晒得那么多粉。固然报春花在我们那儿很少见,也许没有,不像昆明。
1948年3月,香港出了一本《大众文艺丛刊》,撰稿人为党内外的理论家。其中有一篇郭沫若写的《斥反动文艺》,文中说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这对沈先生是致命的一击。可以说,是郭沫若的这篇文章,把沈从文从一个作家骂成了一个文物研究者。事隔30年,沈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却由前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写了序。人事变幻,云水悠悠,逝者如斯,谁能逆料?这也是历史。”
我以为语言具有内容性。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探索一个作者的气质、他的思想(他的生活态度,不是理念)。必须由语言入手,并始终浸在作者的语言里。语言具有文化性。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包世成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有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汁液流转,一枝摇,百枝摇。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国子监,就是从前的大学。
每当家像一个概念一样浮现于我的记忆之上,它的颜色是深沉的。
我每天醒在鸟声里。我从梦里就听到鸟叫,直到我醒来。我听得出几种极熟悉的叫声,那是每天都叫的,似乎每天都在那个固定的枝头。
国子监,现在已经作为首都图书馆的馆址了。首都图书馆的老底子是头发胡同的北京市图书馆,即原先的通俗图书馆--由于鲁迅先生的倡议而成立,鲁迅先生曾经襄赞其事,并捐赠过书籍的图书馆;前曾移到天坛,因为天坛地点逼仄,又挪到这里了。首都图书馆藏书除原头发胡同的和建国后新买的以外,主要为原来孔德学校和法文图书馆的藏书。就中最具特色,在国内搜藏较富的,是鼓词俗曲。
我初学写小说时喜欢把人物的对话写得很漂亮,有诗意,有哲理,有时甚至很“玄”。沈从文先生对我说:“你这是两个聪明的脑壳打架!”他的意思是说着不像真人说的话。托尔斯泰说过:“人是不能用警句交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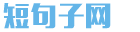 短句子网
短句子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