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语文仿写句子道士塔,你是一段并不遥远的记忆,铭刻着民族瑰宝惨遭
道士塔,你是一段并不遥远的记忆 ,铭刻着民族瑰宝惨遭劫掠的婶婶伤痕。
道士塔,你是一支忧伤的西域怨曲 ,音符中流淌着民族文化被凌辱的怨愤。 道士塔,你是一幅残缺的丑陋画像 ,空白处赤裸裸得暴露着这文明的遗憾。
这样写下去有意思吗?语文教育真该修正下了,答题思路都被限死了。就算把句子造得漂亮得开了花,又有什么意义。
让我自己写的话: 道士塔,你是闪耀着圣光的挪亚方舟,承载了人类文明传承和交流的责任。 这也是我在做作业,要考试我绝对不会写这句,有拿满分的可能,也可能得0分,我不会冒险的,所以我高考语文得了130多,但平时都是80多90分(150满分)。
2.文化苦旅的好句好段
《道士塔》:“道士也有过犹豫,怕这样会得罪了神。解除这种犹豫十分简单,那个斯坦国就哄他说,自己十分崇拜唐僧,这次是倒溯着唐僧的脚印,从印度到中国取经来了。好,既然是洋唐僧,那就取走吧,王道士爽快地打开了门。这里不用任何外交辞令,只需要几句现编的童话。 ”
《莫高窟》:“只记得开头看到的是青褐浑厚的色流,那应该是北魏的遗存。色泽浓厚沉着得如同立体,笔触奔放豪迈得如同剑戟。那个年代故事频繁,驰骋沙场的又多北方骠壮之士,强悍与苦难汇合,流泻到了石窟的洞壁。当工匠们正在这些洞窟描绘的时候,南方的陶渊明,在破残的家园里喝着闷酒。陶渊明喝的不知是什么酒,这里流荡着的无疑是烈酒,没有什么芬芳的香味,只是一派力,一股劲,能让人疯了一般,拔剑而起。这里有点冷,有点野,甚至有点残忍。 ”
《阳关雪》:“从未见过这样完整的天,一点儿也没有被吞食,边沿全是挺展展的,紧扎扎地把大地罩了个严实。有这样的地,天才叫天。有这样的天,地才叫地。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侏儒也变成了巨人。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巨人也变成了侏儒。”“ 在南北各地的古代造像中,唐人造像一看便可识认,形体那么健美,目光那么平静,神采那么自信。在欧洲看蒙娜丽莎的微笑,你立即就能感受,这种恬然的自信只属于那些真正从中世纪的梦魔中苏醒、对前路挺有把握的艺术家们。唐人造像中的微笑,只会更沉着、更安详。在欧洲,这些艺术家们翻天覆地地闹腾了好一阵子,固执地要把微笑输送进历史的魂魄。谁都能计算,他们的事情发生在唐代之后多少年。而唐代,却没有把它的属于艺术家的自信延续久远。阳关的风雪,竟越见凄迷。 ”
《沙原隐泉》:“夕阳下的绵绵沙山是无与伦比的天下美景。光与影以最畅直的线条流泻着分割,金黄和黛赭都纯净得毫无斑驳,像用一面巨大的筛子筛过了。日夜的凤,把山脊、山坡塑成波荡,那是极其款曼平适的波、不含一丝涟纹。于是,满眼皆是畅快,一天一地都被铺排得大大方方、明明净净。色彩单纯到了圣洁,气韵委和到了崇高。”
《都江堰》:“海水是雍容大度的聚会,聚会得太多太深,茫茫一片,让人忘记它是切切实实的水,可掬可捧的水。这里的水却不同,要说多也不算太多,但股股叠叠都精神焕发,合在一起比赛着飞奔的力量,踊跃着喧嚣的生命。这种比赛又极有规矩,奔着奔着,遇到江心的分水堤,刷地一下裁割为二,直窜出去,两股水分别撞到了一道坚坝,立即乖乖地转身改向,再在另一道坚坝上撞一下,于是又根据筑坝者的指令来一番调整……也许水流对自己的驯顺有点恼怒了,突然撤起野来,猛地翻卷咆哮,但越是这样越是显现出一种更壮丽的驯顺。已经咆哮到让人心魄俱夺,也没有一滴水溅错了方位。阴气森森间,延续着一场千年的收伏战。水在这里,吃够了苦头也出足了风头,就像一大拨翻越各种障碍的马拉松健儿,把最强悍的生命付之于规整,付之于企盼,付之于众目睽睽。”
《三峡》:“李白时代的诗人,既挚恋着四川的风土文物,又向往着下江的开阔文明,长江于是就成了他们生命的便道,不必下太大的决心就解缆问桨。脚在何处,故乡就在何处,水在哪里,道路就在哪里。他们知道,长江行途的最险处无疑是三峡,但更知道,那里又是最湍急的诗的河床。他们的船太小,不能不时行时歇,一到白帝城,便振一振精神,准备着一次生命对自然的强力冲撞。只能请那些在黄卷青灯间搔首苦吟的人们不要写诗了,那模样本不属于诗人。”
《洞庭一角》:“范仲淹确实是文章好手,他用与洞庭湖波涛差不多的节奏,把写景的文势张扬得滚滚滔滔。游人仰头读完《岳阳楼记》的中堂,转过身来,眼前就会翻卷出两层浪涛,耳边的轰鸣也更加响亮。范仲淹趁势突进,猛地递出一句先优后乐的哲言,让人们在气势的卷带中完全吞纳。
地是,浩森的洞庭湖,一下子成了文人骚客胸襟的替身。人们对着它,想人生,思荣辱,知使命,游历一次,便是一次修身养性。
胸襟大了,洞庭湖小了。”
3.文化苦旅好句好段评论
重读《道士塔》 一 因为要上《道士塔》的原因,上午上了一节课听了一节课后,不得不坐在办公室里,和余秋雨再做一次迫不得已的交流。
十年前读余的《文化苦旅》时,《道士塔》的印象还是挺深的。作者极尽嘲讽挖苦之能事,对整个民族的悲剧的怜悯痛恨之心,以及余氏特有的看似厚重的文化情绪,当时很是触动。
那时,余秋雨的真实面目我还不是看的很清楚,当他摆起一副渊博厚重的姿势之后,后生小子还真有点爱不释手。那时,一本精装的《文化苦旅》》要二十多元,但我还是忍痛买了,后来余出一本,我买一本,《霜冷长河》《千年一叹》《秋千架》《山居笔记》等等,一路买来,颇花费了我大量的银子。
可惜的是,现在这些书一本本的躺在我的书架上,我再也懒得碰。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是越来越厌恶余秋雨,偌大一个中国,文人无数,余是典型的文人无行,面目可憎;另一方面,这些书都以文化精品的面目出现的,可是现在读他,只觉得暗藏在字里行间的只是摆谱而已,已经读不出半点的文化了。
《道士塔》这篇文章,以前《读者》杂志刊登过,后来收在《文化苦旅》里的《病梅记》《都江堰》《白发苏州》等等好象也都在《读者》上亮过相,余书现在大行于天下,我想和《读者》的一再推崇是分不开的。道士王圆渌的所作所为,后来也在其他的地方见过记载,没有余说的那么糟。
一个穷道士而已,把持敦煌不是他的错,也只是当时的体制,敦煌所在,大漠戈壁,漫漫黄沙,整日面对可怖的石像,腐烂的经书,一般的官员谁愿意去,而且当时,敦煌的卷宗和石像也不像现在是什么什么文化的象征,这些东西后来一批一批被外国人买走、偷走,被他们研究之后才被国人重视,才被称之为“文化”。王道士的所作所为,比起满清王朝北洋军政的租借卖地屠杀国人丧权辱国的行径,只是个小样而已。
可是余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泻”真是有点莫须有。在文章中,余一再写王道士的“卑微、渺小、愚昧”,一再对他揶揄嘲讽挖苦,一再表示对他愤恨,而对来买经卷、偷经卷的斯坦因、伯希和等等描写,作者是一再的写他们的不远万里、风餐露宿、倾家荡产,一再的称他们为学者为专家,一再的写他们对文化研究的热爱。
不经意间,余的用心和骨子里那点货色动已经显山露水了,斯坦因、伯希和等等能算学者专家吗?他们是冒险家,是强盗,他们只是和义律和瓦德西一样的掠夺者。余不把他所谓的满腔怒火向这些人倾泻,而把种种无端的罪归于王道士一人,不知道是什么情结在使然。
这样的文笔做派,这样貌似爱国、爱文化的姿态,这样莫名其妙的情绪,在余的其他书籍里都是一样的,可惜的是,许多人视而不见,以至余书大行特行,为余赚足了银子。 二 敦煌的卷子我在《书法》杂志上读过一些,唐代僧人开始抄的经书也确实令现代任何一个有名的大书法家叹为观止。
一代代的无籍可考的僧人无日无夜的抄录经书,《金刚经》《莲花经》《心经》《观音经》等等,一本本的抄,几千本几万本的抄录,一代代的积压沉淀,一代代的无名的僧人由少抄到老,然后死掉,然后又一代代的僧人接着干,这样的日积月累,就形成了敦煌蔚为大观的经卷,也成就了现在无数学者为之殚精竭虑的敦煌文化。 从1902年王道士把敦煌一个藏经洞的几册经卷送到甘肃学台叶昌炽开始,到1930年近代学者陈寅恪首先提出,敦煌渐成一门学问,称之为敦煌学。
甘肃河西这个地方,原来是有名的河套草原,牛肥马壮,隋以后开始沙化,至唐以后,几个和尚来到敦煌,见此处的石材不错,就挖了几个石窟,躲在里面研究佛教大义。佛家和儒家道家的修行研究形式是不一样的,佛家的修行方式是念经抄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中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于此经受持书写读诵,则为如来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见是人,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 “书写读诵”即能成就这“无量无边功德”,于是抄经读经成了所有僧人的日常作业。
有的僧人一生抄经书无数,至死也没弄明白“明净台、菩提树”,但却积累了书法学、文字学、经学的种种繁荣的端倪。有一段时间,我曾认真的临写过敦煌的明代一无名僧人抄录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这个和尚,穷一生之力抄录《金刚般若波罗蜜经》4万多册,虽没有成佛,但书体的老道精妙,笔势的美妍流畅,已是书之神品。
也难怪敦煌学能够引起国际学界的注意。 三 敦煌学现在的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敦煌遗书、敦煌石窟、敦煌史迹。
当年王道士一块两块的银圆买掉的经卷,已经成了不列颠博物馆的藏品,一册经卷在拍卖场上几百万几千万美元的记录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若是王道士地下有知,不知现在做何感想。王道士是个可怜的道士,生前用经卷换几个铜板以求生计,没有什么民族文化、佛教文化、敦煌文化的概念,余把文物遗失的罪归在他身上,既是王道士的悲剧,也是余秋雨自己的悲剧。
余秋雨作为一个流行的作家,写着流行的文章,论着流行的话题,说着流行的声调,用流行吸引大众的眼球,以买文赚钱卖房卖车住高楼,这本身是没有错的。可惜的是,这个流行的作家定位不够,他偏偏以一个文化人甚至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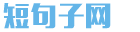 短句子网
短句子网

